夏目漱石与明治新时代“新女性”

夏目漱石,1912年
通常评价,夏目漱石是一位刻画符合明治新时代的“新女性”的作家。其中典型的例子便是《三四郎》 (1908年)中的美弥子。
“pity’s akin to love.”美弥子反复地说。她的发音干净漂亮。
在这短短的一句话中,美弥子作为“新女性”的特点便鲜明地展现出来。她是一位英语发音很地道的女性。《浮云》中的阿势请文三教授自己英语,《魔风恋风》中的初野具有公认的超群的英语能力,《稚儿樱》中以“文明女性”为目标的少女们也学习英语。正如有人指出:“ 作为文明开化的手段,英语占有决定性的比重。”在渴望掌握的西方的“学问”中,人们尤其看重能够流利地使用英语的能力,如能做到则仿佛自己变成了西方人,这种优越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英语能力是“文明女性”身份的象征,美弥子就是其中不折不扣的一员。而且她来往于教会,也被基督教所感化。
不一会儿,响起了唱歌声,想必这就是赞歌了。仪式是在紧闭着高高的窗户的屋子里举行的,从音量听起来好像人数不少。美弥子的声音也夹杂其中。
从农村走出来的三四郎被美弥子所吸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所散发的这种新鲜的“文明”的气息,这是新时代的气韵。这一点和《青春》中的钦哉将女学生繁看成是“明治新时代的风向标”一样。用《理想之佳人》的作者岩本善治的话说,只有像美弥子一样的女性才是“新时代的新日本人理想中的佳人”。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主人公,大多数是类似于美弥子的具有西洋气息的人物,这与镜花所偏好的具有“日本风”的艺妓截然相反。从对美弥子“叱责有艳俗趣味的东西”“当然不同于卑劣的谄媚”等姿态的描写中,可以窥见漱石的意图是将美弥子的魅力定位在与“卑劣的谄媚”的烟花女子不同的类型。“进入明治四十年代,不仅是女性一方,连男性也开始追求‘新女性’。正如有人论述的那样,正因为顺应这种时代氛围,诸如《虞美人草》和《三四郎》之类的小说才博得了以大学生为中心的读者阶层的异常青睐。”漱石文学作品的显著特色之一,便是塑造出取代了艺妓的、具备与“文明”的价值观相匹配的、具有近代教养的全新的主人公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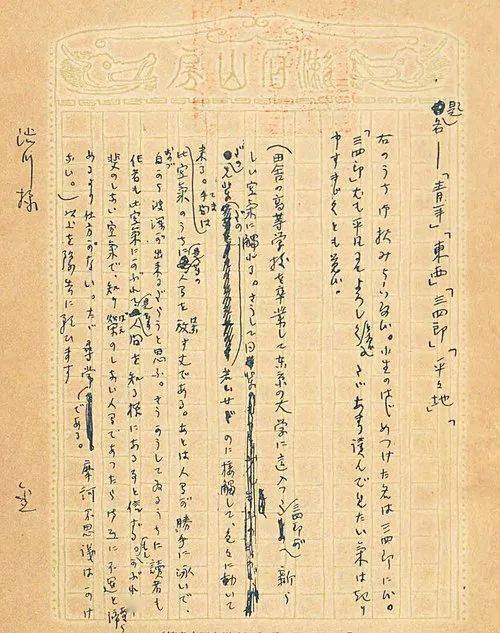
《三四郎》原稿
为了呼应这种主角形象的特点,在漱石的作品中,艺妓和游女只能作为配角处在较低的地位。“都市里的艺妓也是。她们以出卖色相,逢迎谄媚来换取金钱,面对嫖客时,她们除了担心自己的容貌在对方眼中是什么样子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表情。” (《草枕》,1906年)漱石直截了当地道出艺妓的“色气”只是谄媚男人的手段,她们身上不具备任何的主体性。艺妓是“通常只有在男人的目光下才能自我表现的女性”,这种观点与岩本善治“她们只是男人手中玩弄的木偶” (《理想之佳人》)的艺妓观是相通的。值得注意的是,“色”这个词在知识分子的用例中全部剥离了诗的感受性的意味,只具有否定意义。与艺妓“出卖色相”相反,《虞美人草》 (1907年)中的藤尾被刻画成“爱的女王”,作者 将“新女性”的“爱”与艺妓的传统的“色”截然分开,由此可见漱石的主张完全符合“文明开化”时期知识分子中典型的、模式化的女性观。

1966年,东宝株式会社拍摄的电影《夏目漱石的三四郎》海报
在《哥儿》 (1906年)中出场的艺妓也仅仅扮演着愚蠢的丑角。
一个艺妓来到我的面前,抱着三味线对我说:“请您唱点什么吧?”我说:“我不唱,你给我们唱一个吧!”于是她唱道:“金钱呀!太鼓呀!……咚咚锵,咚咚锵,咚咚锵锵,咚咚锵,假如见到走失了的、走失了的三太郎。奴家也要打起鼓,咚咚锵,咚咚锵,四处去找我那有情郎。”她憋足了两口气唱完了这段曲子,然后说:“嗳呀,累坏我了!”既然是累坏了,那唱个容易的岂不是更好?
在这里,“我”听到艺妓唱出的歌词时,想必与《浮云》中阿势听到母亲唱清元时紧蹙双眉的表情一样,只能将其视为“毫无品格”的“色模样”吧。虽然《妇系图》和《日本桥》中的主人公是东京的艺妓,而这里所描写的是地方的艺妓,两者略有不同,但是漱石认为,“二十世纪的诗趣与元禄时代的风流完全不同。文明的诗是钻石,是紫色的,是蔷薇香、葡萄酒和琥珀杯组成的” (《虞美人草》)。因此,在他看来,艺妓的美只是陈腐的江户时代的“风流”,不符合“二十世纪的诗趣”。
诚然,漱石也有让艺妓以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形象出场的作品,那就是《行人》 (1912年)。《行人》前半部主要的插话中,出现了令二郎以及二郎的友人三泽颇感兴趣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实际上就是艺妓。
三泽问道:“她当然不是个良家女子吧?”我虽然把“那个女人”详尽地作了说明,可到底没有“艺妓”这个字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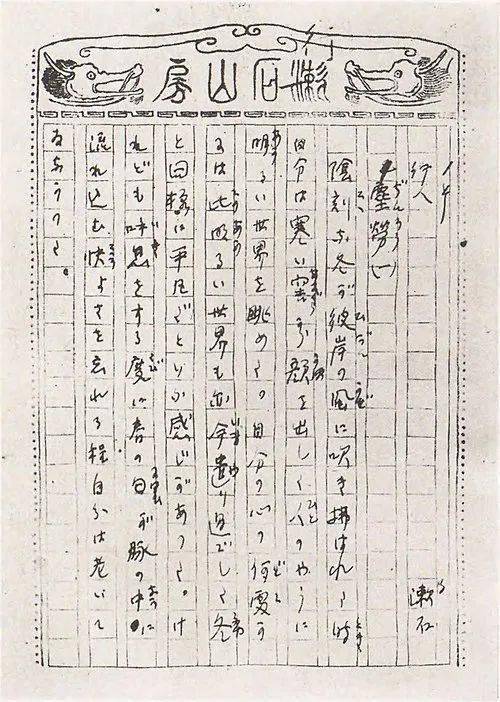
《行人》原稿
二郎坚持规避以“艺妓”这种表述来介绍“那个女人”,可以看出他对“艺妓”这个词的抵触,二郎甚至还表现出蔑视艺妓的态度。然而,三泽和二郎两人却开始留意“那个女人”,并进入了一种竞争状态。正如文中写道:“我对‘那个女人’的兴趣虽然减弱了,却不愿三泽和‘那个女人’打得火热。……这里存在着我们尚未注意到的暗斗。……总之,这里存在着‘性’的争斗。”可见两人双双钟情于“那个女人”,并悄无声息地展开了“暗斗”。但是,他们的感情绝不是“色”,更没有达到“爱”的程度。三泽的态度被描述为:“既不像恋爱,也不是十分热情,除了用“兴趣’二字表达外,再也找不到任何适当的字眼了。”二郎对“那个女人”的关心也被简单地概括为“兴趣的高潮不可能保持那么久”。漱石在作品中并未将艺妓作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使她们完全成为“恋爱”对象 具有“恋爱”的价值。这位艺妓因病卧床时,“ (我)在心中默默地对比着从前锦衣华服、红极一时的艺妓和眼前这位病入膏肓的可怜的年轻女人”。由这一句的描写可见,漱石并非否定镜花式的“美丽艺妓的悲剧”的构思,然而她们绝不能成为小说的中心人物,有关她们的故事自始至终也只是作者埋下的伏笔。在以艺妓作为悲恋物语主人公的作品中,漱石也依旧是一个“文明”人。
然而,虽说是伏笔,她们也一定是使小说主题更为深入、更为细致、更为尖锐的重要伏笔。“那个女人”的存在意义从她与另一位女性,一个离婚后发疯的“姑娘”之间的关联中表露无遗。三泽的父亲曾是因“复杂的情况”而离婚的“姑娘”的媒人,出于这种关系,他将姑娘收留在自己家。那位“姑娘”由于离婚的打击“呈现出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她只对三泽表现出特别的亲近感。“这姑娘说话虽然滑稽可笑,但我外出时却定要把我送出玄关,我即使想偷着出去,她也必然会送出来。而且,一定会说:‘请您早一点回来呀!’”二郎听到那位姑娘所说的话,看到她仿佛把三泽当成自己丈夫的亲密的态度,便询问三泽,那个姑娘“爱上你了吧?”此时,三泽只是冷淡地回应说:“这个嘛,因为是个病人,谁也不知道是出于爱呢还是因为生了病。”然而,当二郎接着追问“难道不是所谓的“色情狂’吗”时,三泽“面色阴沉下来”,断然否定道:“当然不是啦!”
三泽虽然在“恋爱”与否的问题上给出了暧昧的回答,但当“色情”这个字眼时却表现出强烈的拒绝反应。 由此可见明治知识分子典型的对“色”的厌恶感,他们将“色”这个词限定在肉体关系的狭隘的意义上。在断然否定了这种肉体因素后,三泽向二郎坦白,连他自己也渐渐开始被那个姑娘所吸引。那么,三泽为 何会被那个姑娘吸引呢?二郎的哥哥一郎代替三泽给出了答案。
“人在一般情况下,要顾及许多事,比如什么体面啦,情义啦,即使想说也说不出口的,对吧?可是一旦得了精神病,不是就变得相当轻松自在了吗?……那么,一个普通人的责任感肯定都从她的头脑中消失了。……这样看来,她对三泽讲的话比起我们信口寒喧的客套话,不是更富诚意和真心吗?”

明治10年,山梨县府新柳遊廓的艺妓
罹患“精神病”的姑娘的自我表现令一郎感到,那是从一切人世间的情感纠葛中解放出的“纯粹的东西”。三泽的话也印证了一郎的见解,他这样说道:“我开始喜欢那个姑娘了,而且病得越重越喜欢。”发疯程度越强,便越喜欢那个女人。乍一看这种观点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是三泽感到,正如一郎所言,她越发疯,她精神的“纯粹”性越高。“那个姑娘水汪汪的大眼睛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这是她已经患上精神病之后的事”,三泽自己的话也说明了他的心理。三泽从姑娘“水汪汪的大眼睛”中发现的正是一郎所谓的“纯粹”,那是只有“精神病”才可能拥有的心境。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三泽一连串的回答都是由二郎的提问引出来的,二郎问道:“你究竟提出过要娶那个‘姑娘’没有?”可以说,三泽沉醉于那种超越现实的“纯粹”的关系,借用一郎的话说,也就是在不得不介入“体面、情义等”要素的“一般情况下难以体会的关系。那是与世俗的婚姻生活处在不同维度的理想中的关系。因此,三泽冷酷地否定道:“没有提出过结婚。”“据他 (三泽)说,再没有谁能像他那样真诚地在那位年轻美丽的姑娘灵前叩拜了。他的自负来源于确信婚姻这种现实的制度与“纯粹”的灵魂的交流无关。三泽自我陶醉于他与“狂女”的关系中,他的心境与赞美富有诗意的“恋爱”、最终在婚姻中幻灭的透谷尤为相似,他的眼中原本就没有“婚姻”这个概念。
这个姑娘与三泽之间的关系,一如三泽本人的定义,是程度颇浅的“恋爱”,三泽的感情只停留在“喜欢”或是“真诚”之类暖昧的表达。但是,两人的关系明显投射出来自西方的柏拉图式恋爱的理想。在两人不被视为“色情”的关系中,原本就不存在性关系,而是类似于爱情的表现,三泽在她死去时“吻了一下她冰冷的额头”,仅此而已。听到这个故事后,二郎产生了“纯粹且美好”的感受。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三泽与鸥外翻译的作品《两夜》中只用接吻道别的青年士官与少女秦雷希娜,以及《信使》中将对伊伊达小姐的思慕之情只寄托于在她“右手指”上亲吻的日本青年的形象相重叠。上述一系列作品采用的手法是,令男女关系仅限于接吻,并将其作为“纯爱”的象征。而且,鸥外将这些“纯爱”的对象选定为外国女性,漱石也将三泽的恋爱对象“姑娘”的形象与《哈姆雷特》中名为“奥菲利亚”的外国少女的形象重合起来。当二郎看到三泽画的那个姑娘的画像时,他“联想到可怜的奥菲利亚”。而且,那幅画像不是日本画,而是油画。分明是日本女性,却将接吻的对象用油画的形式加以视觉化。 在英国留学期间直接接触到的拉斐尔前派画家们描绘的奥菲利亚像,以及描绘接吻的画作,已然刻在漱石的脑海中,可以说用接吻这种爱情表达方式及其中所象征的对柏拉图式恋爱的美化的源头,是西方文明的影响。亲吻死去的少女的行为类似于理想式恋爱的高潮,极具戏剧化的成分,但是同为戏剧,这里不是“色”的时代的歌舞伎戏剧,而是使人联想到莎士比亚的西洋戏剧的场面。这的确是符合“爱”的时代的舞台设定。

夏目漱石在英国留学期间所居住的公寓
“狂女的纯爱”这种设定,也与《舞姬》中爱丽丝的末路存在共通性。虽然爱丽丝与丰太郎的关系不仅限于柏拉图式的恋爱,但是文中依旧再三地将她写作“少女”,给人留下具有处女魅力的印象。从三泽习惯性地将已经离婚女性的称为“姑娘”“小姐”这一点,隐约可见作者无意识地将她们精神的“纯粹”性与处女的印象相连接的意图。描写因恋爱烦恼而发狂的女性的先例有能乐的《班女》, 但《班女》的主人公是游女,与此不同的是,近代文学中发狂的主人公是具有“少女”气质的女性们。北村透谷认为“高尚的恋爱,应该将其源头置于无污染的纯洁之中” (《论处女的纯洁》),他提出“高尚”的“恋爱”的条件在于肉体的“纯洁”,“处女的纯洁是人类世界的黄金、琉璃、珍珠……可悲的是我国文学的祖先并不懂得尊重处女的纯洁”,他悲叹于日本文学中的主人公鲜有“处女”的形象。似乎是有感于这种悲叹,漱石和鸥外将未婚的处女设定为主人公,或是坚持将肉体上不是处女的女性们塑造成类似于少女的形象,在“处女”的“纯洁”中寄托“纯粹”的“爱”的意象。 漱石将有婚姻经验的“姑娘”的形象与永远是处女的奥菲利亚的形象相重合,说明他受到了基督教的处女崇拜的影响,并试图美化不同于艺妓的、具有处女气质的女性。
然而,漱石却让三泽发出了完全背叛这种“处女”憧憬的言论。
“那个女人的脸,说真的,真像这位姑娘呀!”
所谓“那个女人”就是那个卧病在床的艺妓。从一开始,三泽之所以对“那个女人”感兴趣,无疑是因为她身上有发狂的“小姐”的影子。事实上“小姐”已经亡故,住院的艺妓也不知何时方能痊愈,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 在试图利用“死”和“疯”等非日常的形象描写“纯粹”的“爱”时,意外地出现了一个艺妓的形象,由此可见,日本文学中艺妓的非日常性已然根深蒂固,作家们对此津津乐道。 虽然艺妓被贬低为违背文明的存在,但漱石并未全盘否定艺妓身上所具有的幻想美的力量。

明治末期,被称为“日本第一美人”的人气艺妓万龙
话虽如此,漱石与镜花不同,他无法将彻底地脱离现实的爱的理想寄托在艺妓和游女身上。这是否正是追求“二十世纪诗趣”的漱石的清高之处呢?另外, 漱石无法如镜花一般完全沉溺于黄香梅的世界,他处在更为现实的维度中,渴望看清男女关系的问题。一郎无法认同二郎将三泽与狂女的关系视为“纯粹且美好”的观点,他认为“这话很富有诗意,用欣赏诗的慧眼来看问题才会感到两件事都有意思。可我说的并非这个,而是更实际的问题”。对于一郎来说,比起沉溺于“富有诗意”的世界,他更注重眼前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他切实关心的事是自己和妻子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分歧。 镜花作品的风格呈现出逃离“不纯”的现实,一味沉湎于对美的幻想的倾向,但是漱石试图就婚姻和男女关系的苦恼结合“实际问题”进行描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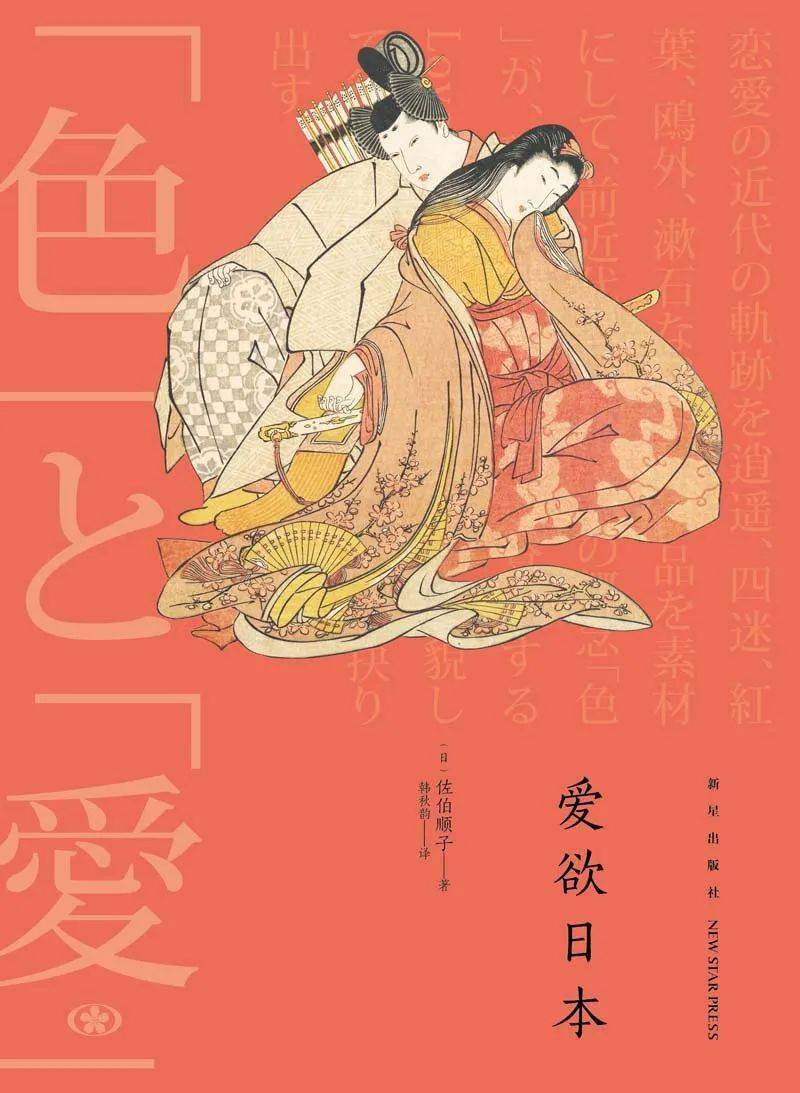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笹川日中友好基金“阅读日本”书系之《爱欲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