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笙: 30年代的农村调查

下一步,就是怎样开展研究工作了。同马季亚尔的争论,一年来时时浮现在我的脑中。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我说得出来,但要拿出充足的证据,又感觉脑中一片空白。对,工作应该从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入手。我们的第一个调查目标是上海日资纱厂,调查包身工制。日纱厂中的包身工,身受帝国主义资本家和包工头的双重剥削。这些包身工,多是贫苦的农家少女,或受骗、或为生活所迫,签订了包身契。一般一包三年。这三年中,她们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全部收入归包工头所有,包工头供给她们仅能活命的衣食,每天却要干12至16个小时的繁重工作,因而许多人死于非命。我们通过调查,收集了大量资料,写出报告,并印成小册子,广为宣传,以唤起广大工人的觉醒。报告指出:“中国经济之衰落,在中国已成普遍之现象。水旱蝗蝻之天灾,兵匪苛税之人祸,物价之飞涨,举债之绝路;凡此种种,驱使大批穷苦无告者群趋城市以供包身制度之牺牲”。这份调查报告所揭露的活生生的现实,刺痛了国民党政府中的某些人,他们声言这个调查是共产党支持搞的,要调查我的背景。蔡元培先生也对我讲,有人反对在日纱厂调查,劝我们改赴农村,去调查农村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立即将调查研究转向农村。
我认识到,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而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因此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学组就拿中国的农村研究作为它的第一步工作。中国地域广阔,农村情况也千差万别,经过分析摸底,我们决定调查从我的家乡无锡开始,然后再扩展到河北和岭南。所以选择这三个地方,是因为江南、河北和岭南是中国工商业比较发达而农村经济变化得最快的地方,假使我们能彻底地了解这三个不同的经济区域的生产关系如何演进,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而对挽救中国农村的危机,也就易于找出有效的办法了。
我先着手组织一个45人的调查团,从1929年7月至9月,对无锡地区22个村进行挨门挨户调查,对55个村进行概况调查,并对8个市镇1204户的经济生活进行调查,同时做了详细记录。
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我们又组织了对广东农村的调查。由于孙夫人宋庆龄的帮助,调查工作得到广东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的协助,调查顺利进行。调查团员由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岭南大学派人组成,首先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16个县进行详细调查,历时三个半月;而后用一个半月时间在番禺10个代表村中调查了1209户。同时进行的还有50个县335村的通信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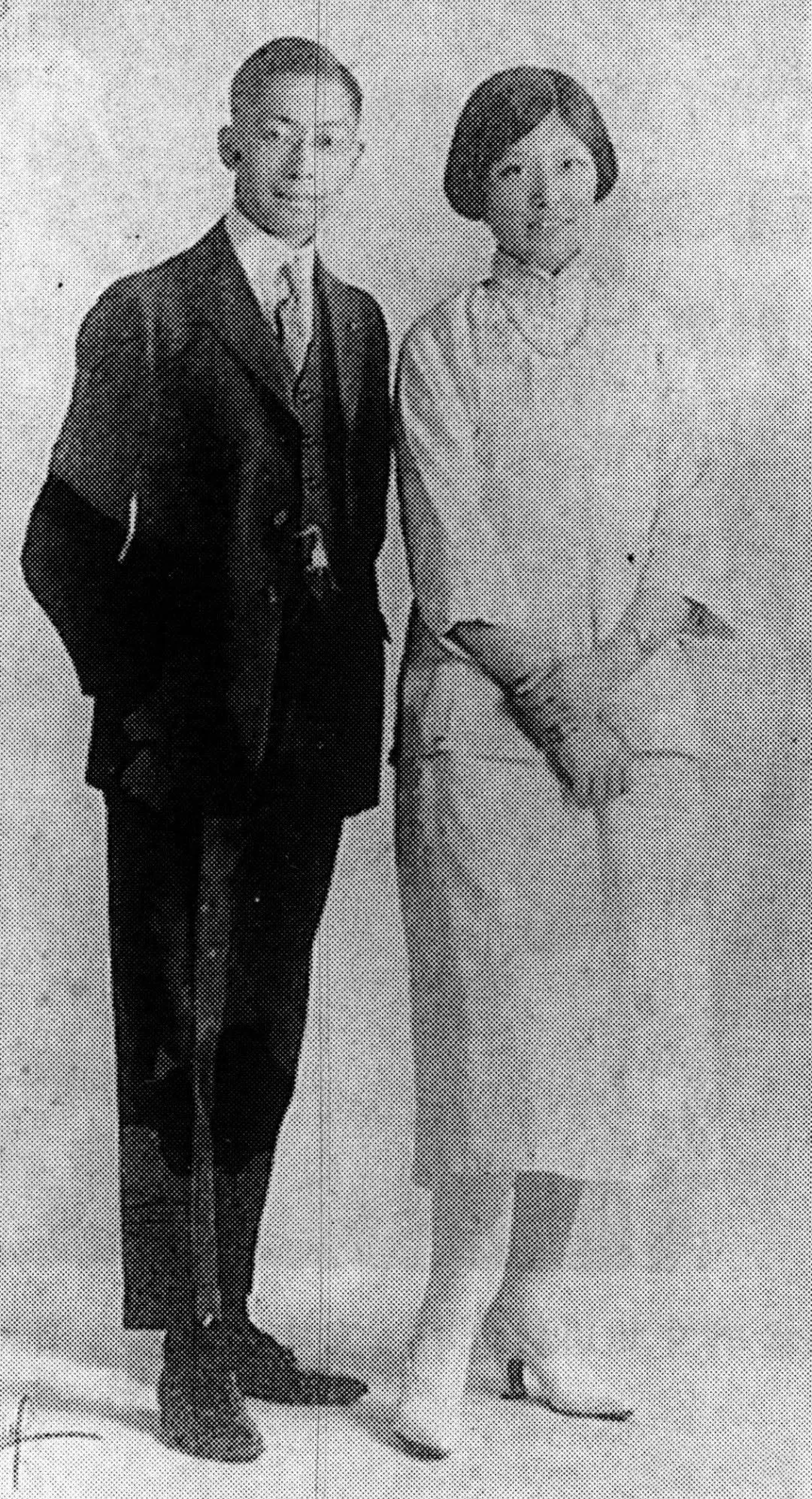
陈翰笙夫妇(1921年)
过去,也有人搞过一些农村调查,不过那是为了慈善救济事业,或为了改良农业,或为了完成某个社会改良的讨论题目而已,这都是些表面的,没能深入下去了解社会结构的本身。而象我们这种深入到农村最低层的大规模农村调查,在中国是一创举。农民和被调查对象对我们的调查也深表怀疑,以为我们也不过做做官样文章罢了。比如,在无锡调查后樟径时,到贫苦的佃、雇农家去,他们不是说没人在家,就是说不懂得。后来想在茶馆中开一个座谈会,他们就大骂我们是“脚客”(即为地主绅士跑腿的),说我们调查他们不怀好意,是要准备抽丁加税的。在任巷调查时,男人不出面,却指使妇女们出来,对我们嘻笑怒骂,无所不至,后来甚至用刷马桶的扫帚向我们调查员的头上乱画。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来解除他们的怀疑和敌对情绪。比如,先让地方行政局将地保们找来,拉拢他们,请他们挨家挨户介绍我们调查的意图,果然消除了许多障碍;乡村的小学教员是村民们尊敬的人物,请他们帮忙解释,一切怀疑就烟消云散了。采取了这一系列办法后,调查顺利多了,所得材料的可靠性约在90%以上。通过对无锡的调查,我们看到:“借贷、押当、起会、放赈等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在无锡农村中具有雄厚的势力,百分之八九的农户差不多都负有债务。近年来,因为战争和农村骚动的影响,乡村资本愈益趋向城市。农户借贷,更加困难。”(《社会科学研究所无锡农村调查记略》)
1929年夏天,我又组织了调查团去营口、大连、长春、齐齐哈尔等地,调查流亡“国内”的东北难民问题。
被天灾人祸逼着,不得不离开本乡,一群一群投奔他处去谋生的人们,普通称为难民。流亡东北的难民一向是山东人最多。据长春总商会会长董立广先生的估计,1927到1929年来长春的难民,山东人占95%强,河北南部人占4%强,其余的是河南、安徽和热河人。近年来,山东、河南的天灾人祸连续不断。水、旱、蝗、雹和兵匪差不多遍地皆是。层出不穷的天灾人祸使大多数人民陷于破产的境地。粮食的缺乏逼着一般的灾民连种子、耕畜一齐吃尽,甚至草根、树皮、滑石粉都用来充饥。求生的希望逼得他们东奔西窜地流亡,地广人稀的东北吸引了大批难民。山东去东北的难民,大部分是凌乱地各自逃生,而河南的则完全是由赈灾会移送去“垦荒就食”的。据了解,从山东三五成群流亡的难民,流亡途中常有被逼卖儿卖女,过后又因悲哀、懊悔、愤懑而自杀的。而被赈灾会移送的河南难民,沿途很难得到饮食,加之风餐露宿,老人、儿童及孕妇等染上疾病,常有死亡的。到了吉黑两省的难民,多数成为雇农和佃农,也有一部分人在铁路上当了苦力,或迫于生机投靠了土匪。
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打算出版一套研究各国生活水平的书,用意在于了解国际资本对各国人民生活的影响。我决定研究一下与国际资本发生联系的烟草生产地区烟农的生活。这年,我带调查组到安徽、山东、河南研讨区做了调查,后因其他事离去,大量的工作由王寅生、张锡昌等同志在1934、1935两年完成,并整理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到1939年,我根据这些调查材料,又在美国搜集了大量的有关资料,写成《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一书,副题为《中国烟农生活研究》。这是用英文写的,它通过研讨这个最典型的商品作物,反映出国际垄断资本同中国的中央政府到地方政权,从军阀官僚到土豪劣绅,直至买办高利贷者互相勾结,剥削压迫农民的真实面目,很有说服力。过去,一般人认为商品作物的推广会有助于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可是,事实上,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种植美国良种烟的大多数是贫农和下中农,而上中农和富农不依靠借贷,也不热心种烟。这是对中国烟草生产区调查的新发现。
从1928年至1934年,在6年的时间里,我们农村社会调查团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脚踏实地的调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加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使我们终于得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结论。大量的调查材料表明,当时的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因此农村的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事实证明,在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农村经济受到帝国主义和农村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面临着破产的威胁。由此我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社会,纯粹的封建已过去、纯粹的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正在转变时期的社会——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前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田地所有者和商业资本及高利贷资本三种合并起来,以农民为剥削的共通的目标。”(《中国田地问题》)过了不久,我更明确地看到中国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后来,主要是旅居国外期间,我就调查得来的材料写了一些论著。1929年写了《亩的差异》、《黑龙江流域的农民和地主》;1930年写了《封建社会的农村生产关系》、《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发轫》、《东北的难民与土地问题》;1934年写成《广东农村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被译成日文);1936年用英文写了《中国南方农业问题》;1940年写了《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1946年在印度用英文写成《中国农民》等等。另外,还写了一些论文,发表在《劳动季刊》、《中国经济》、《农业周报》等报刊上。其他参加调查的同志也写下许多论著。目前,这些调查报告、专著、论文等,已由冯和法同志负责搜集、编排,合为三辑计300余万字的巨著——《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由展望出版社陆续出版。这部巨著的出版,为研究旧中国、研究党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对于广大青年了解旧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也会起一定的启迪、推动作用。

1933年,在农村社会调查的基础上,我同吴觉农、孙晓村、王寅生、张稼夫、钱俊瑞、张锡昌、薛暮桥、孙冶方、冯和法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我被推选为理事会的主席,并一直担任到1951年该会解散。1934年后我在国外期间,由吴觉农代理主席。为了配合农村调查,创办了《中国农村》月刊,登载大量的调查报告和论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中国农村》以合法公开的活动方式,有力地支持了我党的土地革命,对反对封建土地制度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