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旅顺战役日本陆海军矛盾看日本体制合理性
来源: 斐纪岛
1904年夏至1905年初的辽东半岛南端,一场改写远东军事格局的残酷绞杀在此上演。作为沙俄经营十余年的“远东第一要塞“,旅顺港内炮台林立、堑壕纵横,不仅是太平洋舰队的核心母港,更是其远东霸权的军事象征。
日本帝国为争夺东北亚主导权,集中20万兵力对这座钢筋混凝土铸就的堡垒群发起陆海协同总攻。在长达150天的攻防战中,203高地的硝烟遮蔽了黄海的天光,康特拉琴科炮台的废墟浸透了军士的鲜血,双方在不足30平方公里的要塞区域内投入百万发炮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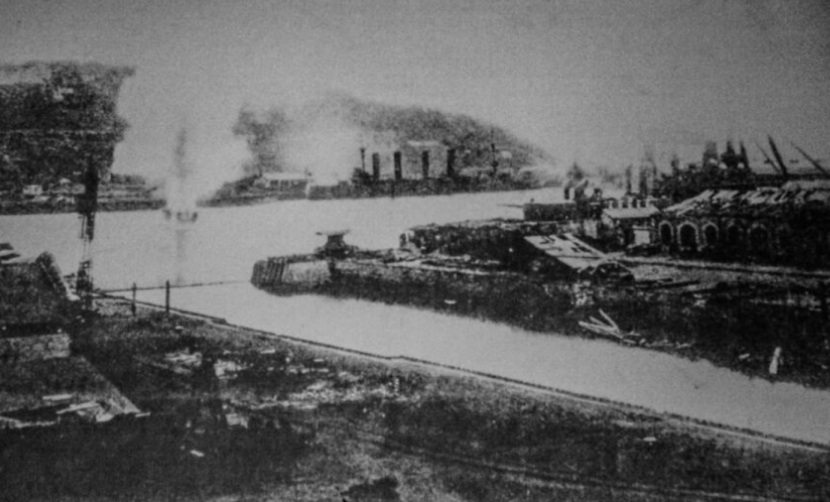
日军以战死5.9万人、伤10万余人的代价,在人类战争史上首次上演了大规模要塞攻坚的血腥范本——这场被称为“旅顺绞肉机“的战役,不仅用刺刀与火炮重塑了近代攻防战术,更以空前的伤亡烈度,为20世纪的要塞战争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血色序章。
而在329天的作战中,日军指挥部内的作战地图上,代表主攻方向的箭头总是如同醉汉般反复游移。
先是用红笔重重圈定东部松树山堡垒群,未及两日又被蓝墨水粗暴覆盖,改向西部二〇三高地集群。在长达五个月的攻坚期间,这种伴随尸山血海而来的战术摇摆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主将乃木希典三次易帅,师团级作战方案推翻重拟达七次之多,各攻击波次在东西两线之间像钟摆般来回震荡。
当二十万日军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钢铁堡垒群前撞得头破血流时,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的“指挥链条震荡“,究竟是困兽犹斗的无奈权变,还是帝国陆海军角力的必然结果?
那些在焦土之上反复涂改的作战方案背后,暗藏着近代化军队转型期怎样的指挥困境?让我们透过历史的硝烟,解析这场要塞绞肉机背后的决策迷局。
一
明治维新后,萨摩藩与长州藩围绕陆海军主导权展开的权力博弈,为日本近代军事史添上了极具戏剧性的浓墨重彩的一笔。1873 年那场震动朝野的“征韩论”,如同一把利刃,无情地割裂了维新核心集团。
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脱胎换骨的变革。在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中,萨摩与长州两藩巧妙借助明治政府大力推行的“四民平等”政策,顺利完成了身份的华丽转型。他们凭借在倒幕战争里积累下的雄厚军事资本,顺势发力,迅速构建起陆海军二元权力格局,在日本近代军事舞台上各自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长州藩以山县有朋为核心灵魂人物,强势主导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进而实现了对陆军的绝对掌控。
从1871年兵部省拆分的关键节点起,直至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长州藩在明治陆军领域的优势愈发显著,近乎达到了压倒性的程度。18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军人敕谕》正式颁布,自此之后,陆军省先后上任的14任大臣里,竟有11位来自长州藩。
其中,山县有朋三度出任陆军大臣,桂太郎、寺内正毅也分别两次担当此要职,他们皆是陆军发展历程中的关键人物,对陆军战略走向、军事制度构建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长州藩同样下足了功夫。陆军士官学校前20期的毕业生中,长州籍学员占比高达37% ,将其他藩阀远远甩在身后。
这些经过系统军事教育的人才,成为长州藩把控陆军的坚实力量。在战争指挥权的分配上,长州藩的优势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甲午战争时期,陆军主力的6个师团指挥官无一例外,全部是长州系将领。他们凭借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强硬的指挥风格,带领部队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为日本陆军赢得了不少关键战役的胜利。
日俄战争期间,黑木为桢、奥保巩等长州将领更是牢牢掌控着满洲军的核心部队,成为左右战争局势的关键力量。长州藩之所以能在陆军领域拥有这般垄断性地位,根源在于山县有朋大力推行的“德国式参谋本部制度”。
通过陆军幼年学校 – 士官学校 – 陆军大学三级培养体系,长州藩成功地将传统武士道精神与先进的近代军事教育深度融合,逐步打造出一个实力强劲、忠诚度极高的“陆军长州阀”。
而在海军领域,萨摩藩则凭借着独特的海洋传统以及与英国教官的紧密合作,通过一系列英国化改革,实现了对海军的全面把控。
从海军省的高层任职情况来看,在先后上任的16任大臣中,有13位是萨摩籍人士。西乡从道、山本权兵卫各自三次担任海军大臣,东乡平八郎也曾出任此职,他们在海军建设、战略规划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海军人才培养摇篮——海军兵学校里,萨摩藩的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觑。前10期毕业生中,萨摩籍学员占比高达58% ,特别是江田岛海军兵学校早期的学员,几乎全是萨摩藩士。这些学员在英国化的教育体系下成长,掌握了先进的海军知识和技能,为萨摩藩在海军中的统治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顾海军的发展历程,1875年是一个关键年份。
这一年,萨摩出身的川村纯义主持海军编制改革,他将萨摩藩原本的水军进行优化整合,改编为常备舰队,迈出了萨摩藩掌控海军的重要一步。
1893年,山本权兵卫推行“六六舰队”计划,彼时海军省80%的课长级官员都来自萨摩藩,他们紧密协作,为打造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而努力。
在实战中,萨摩藩在海军中的优势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甲午战争期间,联合舰队的12艘主力舰舰长中,有9人来自萨摩藩。他们驾驶着战舰,在黄海海域与敌军展开激烈交锋,展现出了卓越的海战指挥能力。日俄战争时,东乡平八郎坐镇旗舰“三笠”号指挥作战,这艘战舰上的所有军官均为萨摩系。他们凭借默契的配合和顽强的战斗意志,为日本海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关键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
二
所以,以萨摩藩为代表的海军,和以长州藩为代表的陆军这两派之间的矛盾,犹如点燃的导火索,从单纯的军事范畴迅速蔓延,深深渗透进日本政治中枢的每一个角落,影响着国家决策的走向。
时间来到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这成为了陆海军对立的关键转折点。
山县有朋亲率长州系陆军,对萨摩叛乱展开残酷镇压。在这场“兄弟阋墙”的内战中,15000名萨摩子弟兵血洒鹿儿岛湾,他们的鲜血染红了这片土地,也加深了两派之间的仇恨与对立。此役过后,陆海军之间的隔阂愈发难以弥合,彼此间的猜忌与争斗愈演愈烈。
1878年,大久保利通遇刺事件如同重磅炸弹,将两派矛盾彻底推向白热化阶段。素有“东洋俾斯麦”之称的大久保利通,在纪尾井坂不幸遭石川县士族伏击。令人瞩目的是,他遇刺时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就有《殖产兴业五年计划》。
大久保利通凭借铁血手段推行改革,触动了萨摩派的根本利益。刺客岛田一郎在供词中直白地表示:“大久保摧毁了西乡公的理想,必须以血偿还。”
这起震惊全国的事件,无情地暴露了明治政府内部存在的结构性裂痕。山县有朋敏锐地抓住这次机会,进一步强化陆军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而萨摩派则通过担任海军大臣的西乡从道,在军事预算方面发起有力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甲午战争期间,陆海军协同问题全面爆发,矛盾公开化。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萨摩派)与陆军大将大山岩(长州派)在朝鲜战场多次产生战略冲突。
海军参谋本部次长桦山资纪(萨摩派)在《战时日志》中详细记载:“陆军要求海军提供仁川港全面护航,却拒绝透露登陆部队具体规模。这种互不信任的状况令人感到窒息。”
黄海海战中,“松岛”号主炮炸膛,致使舰队陷入混乱。事后调查发现,陆军兵工厂提供的炮弹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这无疑成为两派互相攻讦的导火索,双方为此展开了激烈的口水战,互相指责对方的失误与过错。
甲午战争结束后,山县有朋在1896年撰写的《军备意见书》中尖锐指出:“海军陶醉于大东沟的胜利,却忽视大陆扩张的根本需求。”
萨摩派则通过《海军时报》迅速反击:“陆军在辽东半岛的伤亡率是海军的三倍,证明其战术思想落后于时代。”
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这种对立态势在日俄战争前达到顶点。1903年御前会议上,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萨摩派)与陆军大臣寺内正毅(长州派)就旅顺要塞主攻方向爆发激烈争吵,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最终无奈之下,只能由明治天皇亲自出面裁定作战方案。
对于这段历史,历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军国主义》中深刻剖析道:“萨摩与长州的矛盾本质是海洋扩张与大陆政策的路线之争,这种二元对立塑造了日本近代军事体制的致命缺陷。”
信夫清三郎在《日本陆海军史》中也进一步指出:“两派争夺的不仅是军费分配,更是对明治国家发展方向的话语权。”萨摩藩与长州藩之间的权力博弈,深刻影响了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成为理解日本军国主义兴衰的关键所在。
三
在日俄战争的宏大历史叙事中,日本陆海军围绕金州地峡展开的战略博弈,犹如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力角逐大戏,无情地撕开了萨摩与长州两大藩阀集团之间隐藏已久的结构性矛盾。
这一矛盾并非浮于表面的战术分歧,而是深植于军事战略底层逻辑的根本性对立,其影响如涟漪般层层扩散,深深烙印在战役进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甚至改写了整个战争的最终结局,成为日本近代军事史上一道难以磨灭的裂痕。
彼时,陆军高层目光紧盯着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全线通车这稍纵即逝的战略窗口期,视金州地峡为扭转战局的关键枢纽。山县有朋在《对俄作战意见书》里,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着重写道:“金州地峡堪称满洲战场的咽喉要地,一旦掌控此处,便能如庖丁解牛般,将俄军主力切割为彼此孤立、无法呼应的两大部分。”
基于此战略构想,黑木为桢所率的第一军领命奔赴奉天方向,承担起牵制俄军主力的艰巨任务;而奥保巩的第二军与乃木希典的第三军则剑指金州地峡,全力执行切断旅顺俄军陆上补给线的关键使命。
这种“关门打狗”式的精妙布局,背后涌动的是长州系陆军对大陆版图扩张的强烈渴望与野心,他们试图借由这场战争,在东亚大陆上勾勒出日本陆军势力的新版图。
反观海军,其战略核心却聚焦于截然不同的方向。萨摩系海军将领东乡平八郎在精心拟定的《海军作战纲要》里,反复强调:“制海权无疑是左右整场战争胜负的命门所在,唯有彻底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方能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主动权。”
为达成这一目标,联合舰队在战争伊始便孤注一掷,对旅顺港发动了三次规模浩大的闭塞作战,妄图通过沉船堵港的决绝方式,将俄国太平洋舰队困死在旅顺港内。
然而,事与愿违,这些作战行动均以失败告终,不仅未能如愿封锁港口,反而促使俄军警觉,进而大规模加固旅顺港周边的陆上防御工事,使得后续作战难度呈几何倍数增长。
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在1904年6月的御前会议上,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公然将矛头指向陆军,言辞激烈地斥责道:“倘若第三军能够尽早攻克旅顺,又怎会让海军在此过程中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这番指责,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陆海军之间矛盾的千层浪。
随着战争的推进,陆海军之间的战略分歧在金州地峡战役中彻底白热化。
1904年5月26日,奥保巩所率的第二军在进攻南山要塞时,遭遇了俄军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南山要塞作为俄军精心构筑的防御堡垒,配备了多达44门重炮以及12挺马克沁机枪,这些武器相互配合,形成了密不透风的交叉火力网,将进攻的日军死死压制。
多年后,陆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在回忆录中仍满是遗憾地感慨道:“若是海军当时能够提前对南山炮台展开炮击,为第二军扫除火力障碍,那么第二军在此次战役中的伤亡至少可减少三分之二。”
然而,海军方面却以“舰队需时刻防范海参崴俄军突袭,无法抽调兵力支援陆地作战”为由,果断拒绝了陆军的支援请求。在孤立无援的绝境下,第二军只能凭借血肉之躯强攻南山要塞,最终付出了1.1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才艰难地占领了金州地峡。这一战役的惨痛教训,无疑成为了陆海军矛盾激化的催化剂,让双方之间的嫌隙愈发难以弥合。
四
到了旅顺作战,日本陆海军的战略部署与博弈,背后潜藏着萨摩与长州两大藩阀集团根深蒂固的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的地步。无法调和。
长州系陆军以山县有朋为核心,其战略思维深受大陆扩张理念的熏陶。在旅顺作战期间,他们将“切断旅顺俄军陆上补给线”作为核心战略。
奥保巩率领的第二军沿着金州地峡稳步推进,目标紧紧锁定东部的凤凰山、二龙山堡垒群。
在他们的规划中,只要成功扫清这些外围据点,便能打通进攻松树山、东鸡冠山等核心阵地的通道,进而实现对旅顺俄军的全面围困与打击。
然而,萨摩藩阀长期以来对长州系独揽军权一事耿耿于怀,充满戒备。明治天皇出于平衡各方势力的考量,任命萨摩籍的大山岩为满洲军总司令。
表面上,大山岩肩负统一指挥陆海军的重任,但实际上,这一任命更像是在长州系与萨摩藩阀之间放置了一个制衡的砝码,以防止山县有朋权力过度膨胀。陆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在其《满洲征战日志》里,便隐晦地揭示了其中的微妙关系:“大山岩元帅的司令部与东京参谋本部之间,始终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紧张氛围。萨摩派屡屡提出调整主攻方向的要求,其真实目的不言而喻,无非是担忧长州系在战争中获取过多胜利果实,进而巩固其在军界的绝对统治地位。”
海军方面,萨摩系的东乡平八郎舰队在作战初期,坚定执行“沉船堵塞港口”的战术。他们企图通过这一决绝的手段,将俄国太平洋舰队死死封锁在旅顺港内,使其无法出海作战,然后静候陆军成功歼灭东部堡垒群的俄军主力,再进行下一步行动。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残酷。日俄战争时,日本海军为控黄海制海权、困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对旅顺港发动三次自杀性闭塞作战,均失败。
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海军为掌控黄海制海权并围困俄国第一太平洋舰队,对旅顺港发动三次自杀性闭塞作战,均以失败收场。
1904年2月20日,首次作战开启,5艘由民用船改造的船只搭载77名志愿兵从仁川港出发,可23日便遭俄军炮击,还没到达预定位置就被迫全部自沉。
3月23日,第二次作战打响,东乡平八郎派遣驱逐队掩护4艘轮船。然而俄军早有戒备,“千代丸”被炮火击沉,“福井丸”被鱼雷击中,广濑武夫在搜救部下时不幸战死,“弥彦丸”与“米山丸”同样被击沉,此次作战日军仅15人死伤 。
5月3日凌晨,第三次作战开始,8艘船搭载159人出发,却因风浪导致队形散乱,随后遭沙俄炮击,6艘船被击中或触雷,2艘虽自爆但位置偏离航道,此次作战日军损失惨重,60人阵亡、32人被俘。
这三次作战不仅消耗了日军大量人力、物力,还未能实现封堵港口、困住俄国舰队的目标,成为日军战略上的重大挫折。特别是俄国太平洋舰队马卡洛夫上任后,大力整顿舰队纪律,强化训练,将技术与战术有效融合,展开卓有成效的反击,直接导致日军闭塞作战彻底失败。
时任海军省次官的斋藤实,作为萨摩派的一员,在给山本权兵卫的密信中无奈地承认:“马卡洛夫中将率领的俄军舰队突然发动反击,我方的作战部署被完全打乱。‘福井丸’等5艘闭塞舰在老铁山海域瞬间被击沉,370名萨摩籍水兵就此葬身海底,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与此同时,陆上战场的局势也陷入了胶着状态。康特拉琴科少将指挥下的俄军,在东鸡冠山阵地精心构筑了七层铁丝网,还配备了威力巨大的180毫米臼炮集群。
乃木希典率领的第三军在6月发动首次总攻时,尽管付出了1.7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却仅仅向前推进了500米。
山县有朋在《对俄作战备忘录》中,罕见地对萨摩派提出了严厉批评:“海军一门心思沉迷于港内封锁的计划,却忽视了对陆军侧翼的掩护,导致陆军在进攻东部堡垒群时孤立无援,久攻不下,实在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随着战争的持续推进,萨摩藩的不满情绪在8月的御前会议上彻底爆发。
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毫不留情地直指陆军作战存在的严重失误:“第三军在进攻二龙山时,竟然损失了23门野炮,这一数字相当于整个关东州战场火炮储备的40%。以这样低效的攻坚能力,又怎能顺利切断中东铁路,实现对俄军的战略包围呢?”
他当场提议将主攻方向转向西部高地,认为那里或许存在着突破俄军防线的契机。然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长州系将领寺内正毅的强烈驳斥:“随意变更既定的作战计划,这分明是萨摩派缺乏战略定力的表现。如此朝令夕改,只会让整个作战陷入混乱,前功尽弃。”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大山岩不得不从中调和,裁定采取“东西两线交替强攻”的策略。但这一折中的决定,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使得日军在9月的第二次总攻中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困境,兵力与火力被分散,单日伤亡人数迅速突破9000人。
英国军事观察员伊恩·汉密尔顿在其《日俄战争目击记》中,一针见血地评价道:“所谓的‘满洲军司令部’,实际上已然沦为萨摩与长州两派争权夺利的角力场。
大山岩手中的帅印,与其说是指挥作战的象征,倒更像是天皇用来平衡藩阀势力的一个工具,根本无法真正实现陆海军的统一指挥。”
到了10月,这种体制性的内耗愈发严重,达到了顶点。当陆军请求海军抽调“三笠”号上的主炮支援东鸡冠山的进攻时,东乡平八郎却以“海参崴舰队可能突袭”为由,果断拒绝了这一请求。
这一拒绝直接导致俄军得以通过未被切断的铁路,顺利获得2万吨弹药补给,进一步巩固了其防御力量。
萨摩派的喉舌《海军时报》趁机公开嘲讽:“长州式的‘肉弹冲锋’战术,在俄军坚固的混凝土工事面前,早已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与其继续在东部战场无谓地消耗兵力,倒不如将第三军改编为海军陆战队,由联合舰队直接实施登陆作战,或许还能找到破局的办法。”
而长州系也不甘示弱,通过《陆军新闻》予以反击:“若没有陆军在金州拼死拖住3万俄军,海军的封锁线恐怕早就被马卡洛夫率领的舰队冲破了。萨摩派整天鼓吹的海权论,在现实面前,不过是一座不堪一击的沙滩城堡罢了。”
双方的矛盾不断激化,相互拆台的局面愈演愈烈。最终,明治天皇不得不派遣侍从武官长冈泽精一郎亲赴旅顺督战,才勉强压制住两派即将公开决裂的态势。然而,经此一役,陆海军协同作战的裂痕已然深深扎根于旅顺战场的每一寸土地,成为影响后续作战的巨大隐患。
回顾这段历史,不难发现这场陆海军的博弈,本质上是萨摩与长州两大藩阀集团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
井上清在《日本军国主义》中深刻剖析道:“萨摩与长州之间的矛盾,其根源在于海洋扩张与大陆政策这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线之争。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面,从根本上塑造了日本近代军事体制的致命缺陷,使得日本在军事决策与作战指挥上,始终难以形成统一而高效的体系。”
信夫清三郎在《日本陆海军史》中也进一步指出:“两派之间的争斗,绝不仅仅局限于军费分配这一物质层面,更深层次的是对明治国家未来发展方向话语权的激烈争夺。这种矛盾贯穿了日本近代化的整个进程,从日俄战争一直延续到二战末期,始终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的战略决策,成为后人理解日本军国主义兴衰历程的关键所在。”
五
在面临着俄罗斯海上,陆地支援兵力的威胁下,乃木希典所指挥的第三军,协同第二军及其所属师团,在这场战役中深陷指挥泥沼。
根据星野金吾与松井石根合著的《日俄战争史》,日军参谋于南山坡山(海鼠山,海拔183米 )进行侦查作业时,敏锐察觉到203高地蕴含的巨大战略价值。
大山岩作为日军重要将领,迅速捕捉到这一关键信息,果断下令进攻203高地。然而,乃木希典却执着于东部堡垒群作战,固执己见地拒绝转移兵力,坚持对松树山、二龙山、东鸡冠山等东部堡垒群展开攻击。
长冈外史,这位时任参谋次长,在他写给井口省吾(满洲军总务课长)的书信里,详尽记录了这一时期指挥体系的紊乱: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龟缩于旅顺外港,使得日军进攻西部堡垒群的行动收效甚微。
在此情形下,山县有朋转而强令乃木希典回师进攻东部堡垒群。激烈而残酷的攻坚战斗旋即爆发,日军在俄军严密布置的铁丝网、密集的机枪火力以及坚固工事的阻挡下,伤亡极为惨重,战场上一片狼藉。
黄海海战之后,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突围失败,被日军拦截后被迫退回旅顺港,而此时波罗的海舰队正迅速南下,逐渐逼近远东地区。
这双重海上威胁如同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得日军高层不得不频繁调整陆战策略。大山岩基于全局战略态势考量,再度严令进攻203高地,试图通过掌控这一制高点,实现对旅顺港的有效封锁,从而掌握战争主动权。
从诸多军事史文献资料中能够发现,这一阶段作战指令变更极为频繁,海陆军之间的协同矛盾也彻底暴露。
乃木希典的指挥权先后三次被临时调整,作战计划在东西部堡垒群与203高地之间来回变动。后世战史研究者普遍指出,日军在陆地攻坚与海上封锁的双重压力之下,完全陷入被动应对的艰难困境。
他们既要承受东部堡垒群俄军的顽强抵抗,又要因波罗的海舰队的步步紧逼而仓促改变作战方向。
第一次、第二次进攻203高地时,日军都存在兵力未充分集结、火力支援严重不足的问题,这直接导致部队在棱线争夺过程中遭受重大伤亡。
长冈外史等亲历者的记录也进一步证实,这种因战场形势急剧变化而不断推翻原有作战部署的指挥模式,尽管是日军面对多重危机时的无奈之举,但却极大地加剧了前线作战的混乱局面,使第三军在反复的拉锯战中付出了远超预期的惨痛代价,成为日俄战争中“人海战术” 与 “指挥失调” 相互叠加的典型悲剧性战例。
军事历史学家大江志乃夫在其著作《日俄战争军事史研究》中明确指出,乃木希典所秉持的“正攻法” 在旅顺战役中暴露出严重的战术滞后性。
彼时,俄军依托旅顺要塞号称“东洋第一” 的防御体系,配备高压电网、马克沁重机枪以及多达500余门火炮,构建起多层次交叉火力网。
反观日军,由于缺乏重炮支援,只能沿用传统的步兵集团冲锋战术。在俄军强大的火力面前,日军士兵如同飞蛾扑火,进攻场面极为惨烈,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吉辰在《从几个侧面看日本的甲午、日俄战争军事史研究》中进一步剖析,乃木希典对俄军防御工事的错误判断,以及对“肉弹战术” 的盲目迷信,致使第三军在9月战役中付出了7500余人伤亡的沉重代价,却仅仅夺取了203高地外围的少量零星据点。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海陆军之间的战略分歧在第二次进攻203高地时达到了顶点。
依据《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史》记载,海军军令部长东乡平八郎多次向陆军施加压力,迫切要求尽快攻克旅顺,以此解除波罗的海舰队带来的巨大威胁。
但乃木希典却依旧坚持“逐步蚕食” 东部堡垒群的既定计划,与大山岩 “集中兵力突破203高地” 的战略构想产生了激烈冲突。
这种指挥权的频繁更迭以及作战目标的反复摇摆,饱受诟病。军事评论家司马辽太郎在《乃木希典传》中言辞尖锐地批评道:“将校无能,累死三军”,认为日军高层的战略短视以及战场指挥的严重割裂,使得旅顺战役沦为一场 “用士兵的血肉填补决策漏洞的悲剧” 。
除此之外,俄军的防御策略以及日军的情报失误进一步加剧了战场的混乱状况。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黄海海战失利后退回旅顺港,为增强陆地防御力量,他们拆卸舰炮用于陆防,将旅顺要塞的火力密度提升至每公里正面40门火炮。
而日军参谋本部对俄军防御工事的情报掌握严重不足,甚至犯下“误判203高地为普通丘陵” 这样的低级错误。
正是由于这种情报上的巨大盲区,导致乃木希典在第二次进攻时,仍然将主攻方向集中于东部堡垒群。直到长冈外史等前线参谋通过南山坡山的观测,才发现203高地的关键战略价值,进而迫使大山岩强行干预作战计划。

随着波罗的海舰队加速东航,日军所面临的作战压力达到了临界点。英国学者Richard Connaughton在《The War of the Rising Sun and Tumbling Bear》中分析指出,日本联合舰队若无法在波罗的海舰队抵达之前歼灭旅顺港内的俄舰,就极有可能面临被两线夹击的致命危险。
这种紧迫感使得日军大本营在9月战役期间连续三次变更作战指令,甚至出现了 “陆军尚未完成部署即被强令进攻” 的荒唐局面。
军事史学家潘茂忠在《日俄战争陆战史》中指出,这种“为时间而战” 的被动局面,使得日军在第二次进攻203高地时,只能以血肉之躯去对抗俄军坚固的钢铁堡垒,单日伤亡人数瞬间突破3000人,战况之惨烈可见一斑。
正如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
旅顺战役中所呈现出的指挥混乱与战略失误,从本质上讲,是日军在多重危机逼迫下的无奈反应。
乃木希典的战术保守、大山岩的战略急躁、海陆军之间的协同失效,以及情报体系的全面崩溃,共同交织成这场“绞肉机战役” 的悲剧性底色。
日本军事史学者长南政义在《依据新史料的日俄战争陆战史》中深刻指出,日军在旅顺战役中的决策困境,是“资源有限性与战略目标无限性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 。这种矛盾在波罗的海舰队逼近的严峻形势下被无限放大,迫使日军在情报匮乏、装备落后的不利条件下仓促应战,最终以数万士兵宝贵的生命为代价,艰难换取战略上的主动权。
不可忽视的是,日军在这场战役中的被动应对,不能完全归责于指挥层的无能。
军事历史学家潘茂忠在《日俄战争陆战史》中着重强调,乃木希典的“肉弹战术” 在当时的军事理论框架下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面对俄军坚固的防御工事,日军因缺乏重炮支援,无奈之下只能依靠步兵集团冲锋来尝试突破防线。
这种战术虽然在旅顺战役中暴露出致命缺陷,但在甲午战争时期却曾发挥过一定作用。此外,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情报失误以及海军施加的战略压力,从客观上极大地压缩了第三军的战术选择空间。
从国际战略层面来看,日本的困境更显得无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分析认为,日俄战争是 “新兴帝国与传统帝国在远东的激烈碰撞”。
日本作为后起的新兴帝国,迫切需要在短时间内击败俄国,从而确立其在亚洲的霸权地位。然而,俄国凭借其广袤的领土和丰富的资源储备,具备承受长期战争消耗的能力。这种巨大的战略紧迫性,使得日军在旅顺战役中不得不采取冒险战术,甚至不惜以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来换取时间上的优势。
总而言之,旅顺战役中的指挥混乱与战略失误,本质上是日军在多重危机下的被迫反应。
乃木希典的战术保守、大山岩的战略急躁、海陆军的协同失效,以及情报体系的全面崩溃,共同构成了这场“绞肉机战役” 的悲剧性底色。
六
1905年1月2日,凛冬的寒风凛冽地呼啸于旅顺战场,一场足以左右旅顺命运走向的战役在此轰然打响。
乃木希典所率的第三军,对203高地发起了第三次总攻。
回溯至首次进攻,已过去漫长的两个多月,在这段惨烈的鏖战时光里,日军折损极为惨重,累计伤亡人数竟高达5.9万人,战场之上,残肢断臂与鲜血交织,诉说着战争的残酷无情。
依据详实的《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史》记载,自1904年11月起,乃木希典便被卷入了大山岩(时任满洲军总司令)与山县有朋(陆军参谋总长)战略分歧的巨大漩涡之中。
大山岩认为,必须集中优势火力全力突破203高地,以此掌控港口,从而掐住海上交通的咽喉。
而山县有朋却主张优先歼灭东部堡垒群,诸如松树山、东鸡冠山等地的俄军主力,以稳固陆上作战的根基。这一分歧在12月的作战会议上彻底激化,达到顶点。
从乃木希典彼时的日记中,便能深切感受到他内心的煎熬与无奈,他写道:“左右皆为军令,进退皆无完策,唯有以死谢罪。”
而他随身携带的《叶隐闻书》扉页上,那刺目的血书“不成功便成仁” ,更是将他抱定必死决心、欲亲率敢死队冲锋的心境展露无遗,一位深受武士道精神浸润、在两难抉择中走向极致的将领形象跃然眼前。
12月15日,日军大本营做出一项极具戏剧性且影响深远的决策,任命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临阵接管第三军的指挥权。此决定一经公布,犹如巨石投入平静湖面,激起千层浪,引发后世史家旷日持久的争论。
军事史学者大江志乃夫在《日俄战争全史》中,通过查阅陆军省档案披露,山县有朋对乃木希典“过度服从大山岩”的不满早有记录。
在12月12日的参谋本部会议上,山县派中坚人物上原勇作言辞激烈地直言:“若再这般纵容乃木的‘武士道蛮勇’,整个满洲战局恐怕都将被拖垮。”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山岩的副官辻政信在回忆录中称,当时的乃木希典已然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每日仅仅能睡3个小时,指挥图上布满了指甲掐出的血痕”,所以此次换将实则是为了“拯救其名誉的无奈之举”,是在绝境之中对乃木希典的一种保全。
儿玉源太郎接手指挥权后,迅速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果敢的决策力。
他即刻启用从本土紧急调来的280毫米榴弹炮与240毫米加农炮,其战术日志中清晰记载:“若再迟三日,第三军恐将彻底丧失攻坚能力。”为提升炮击的精准度,他大刀阔斧地重组炮兵观测体系,在南山坡山(海鼠山)建立前沿指挥所。
自此,日军首次实现了对旅顺港内俄舰的精准炮击。英国随军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里森在《泰晤士报》的战地通讯中,以亲眼所见为这场激烈战斗留下生动注脚:“日军在12月28日的炮击持续了整整48小时,203高地的顶峰被硬生生削低3米,俄军那看似坚不可摧的混凝土工事,在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如同融化的黄油般轰然崩塌。”
这震撼的场景,既彰显了战争的暴力美学,更凸显出儿玉源太郎战术调整的显著成效。
关于此次临阵换将的动机,各界观点不一,众说纷纭。
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提出独特见解,他认为这一事件实则是明治陆军内部“长州派”与“萨摩派”权力博弈的集中体现。
乃木希典身为山县有朋的长州嫡系,在旅顺战役中却倾向于大山岩(萨摩派)的速胜战略,这种派系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最终迫使大本营不得不以“战术调整”的名义介入,平衡各方势力,确保战争的走向契合日本的战略利益。
而美国学者爱德华·德雷尔在《日俄战争中的日本陆军》一书中,则更侧重于从实战因素剖析,他指出乃木希典一直秉持的“肉弹战术”在这场战役中已被证明彻底失效,无数日军士兵的生命消逝在俄军坚固的防线前;而儿玉源太郎所倡导的“炮火决胜论”,才是打破当前战争僵局的关键所在,是引领日军走向胜利的正确路径。
1905年1月2日清晨,熹微的晨光刚刚洒落在203高地上,一场惊心动魄的白刃突击在此展开。
据参战者冈玄次郎在《旅顺阵中记》里的详尽记载:“儿玉司令官身先士卒,亲率后备队冲锋陷阵,而乃木大将试图阻止,却被众人按倒在指挥所内。”
这一描述将当时紧张激烈的场景鲜活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当日16时,经过一番浴血奋战,第三军终于成功控制高地主峰。
随军摄影师秋山徳藏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定格了那残酷又震撼的瞬间:“山顶工事内的俄军士兵尸体呈跪射姿态,枪管因长时间射击发热而扭曲变形。”这些照片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对战争残酷性的无声控诉。
攻克203高地后,日军迅速在高地上建立观测所,这个观测所宛如一只高悬的“死亡天眼”,严密监视着旅顺港内俄舰的一举一动。
海军军令部档案清晰显示,在1月3日至5日期间,联合舰队借助203高地观测所提供的精准情报,仅用89发240毫米炮弹,便成功击沉俄舰“佩列斯韦特”号,并重创“波尔塔瓦”号。
东乡平八郎在给儿玉源太郎的电报中,毫不掩饰对高地炮兵的倚重与感激:“若无高地炮兵的支援,帝国海军或将在未来面对波罗的海舰队的完整编队,后果不堪设想。”
而早在1904年12月20日,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马卡罗夫在日记残页中就曾精准预言:“一旦203高地失守,港内舰队将彻底沦为任人宰割的活靶。”一语成谶,命运的齿轮无情转动,见证着战争的胜负更迭。
这场战役虽以日军的胜利告终,但其后遗症却延续至今。
日本防卫省战史室所藏的《第三军机密作战日志》透露,在换将过程中,内部曾就“是否追究乃木责任”展开激烈争论。
有人认为乃木希典指挥不力,致使日军伤亡惨重,理应承担相应责任;但也有人念及他的忠诚与付出,主张从轻发落。
最终,在山县有朋“保留其职”的意见主导下,这场争论才尘埃落定。
军事评论家秦郁彦在《日俄战争史的真相》中,对这场战役做出深刻总结:“203高地的攻克,既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战术胜利,也是日本陆军指挥体系的一次深刻变革,宛如一场外科手术——用儿玉的理性切割乃木的偏执,用派系之间的妥协换取战场的转机。”
当硝烟逐渐散去,疲惫不堪的日军士兵在高地战壕中,发现了俄军工兵留下的一句俄语涂鸦:“你们得到的只是石头,我们守住的是荣耀。”
这句简短却有力的话语,宛如一声穿越时空的叹息,成为日俄双方在这场堪称绞肉机的战役中悲壮命运的生动注脚,既展现了俄军虽败犹荣的坚守精神,也凸显了战争的荒诞与无奈。
与此同时,在儿玉源太郎“以火力换时间”战术思想的引领下,日军对东部堡垒群发起凌厉攻势。
12月18日13时10分,东鸡冠山北堡垒在2300公斤炸药的强大威力下被成功引爆,剧烈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响彻天际,第11师团趁势而上,于19时顺利占领该堡垒。
12月28日9时,二龙山堡垒在2840公斤炸药的爆破攻击下,防线彻底崩溃,第9师团随后攻克该堡垒;12月31日9时,松树山堡垒遭遇3700公斤炸药的毁灭性打击,仅仅半小时后,第1师团便宣告占领该堡垒。
这一系列高效的军事行动,不仅有力地印证了儿玉源太郎战术思想的正确性与前瞻性,凭借强大的火力优势,日军在短时间内迅速突破俄军防线,大大缩短了战争进程,也为乃木希典重新赢得指挥权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后,乃木希典重新回到指挥岗位,带领第三军继续在战场上纵横驰骋。
随着东部堡垒群的相继瓦解,第三军主力于1905年1月下旬踏上北上之路,全力支援奉天会战,与满洲军主力成功会师。此时,日本联合舰队也在海上严阵以待,时刻警惕着远道而来的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
英国战略学家李德·哈特在《战略论》中深刻指出:“旅顺战役的胜利,不仅解除了日本长期以来面临的海上威胁,让其海军得以在太平洋上自由驰骋。更重要的是,它重塑了整个远东地区的权力格局,深刻影响了此后的历史走向。”
然而,这一切荣耀的背后,是日军在旅顺投入的13万兵力以及5.9万人伤亡的沉重代价,是无数家庭的破碎与离散。
而俄军旅顺要塞司令斯特塞尔在投降书中写下的那句哀叹:“我们输掉了一场本不该输的战争。”更是让人不禁对战争的胜负、意义与价值产生深深的思考,战争的残酷与无常,在这一刻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七
需要明确的是,在旅顺战役期间,乃木希典指挥下搞出来的“肉弹攻势”。一直被诟病。甚至认为乃木希典的前三次攻势是白白的浪费士兵生命的徒劳无谓的进攻。
不过从实际作战效果来看,这一战术实实在在地对俄军的防御体系产生了持续性的消耗。
依据《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战史》的记载,1904年8月的第一次总攻里,日军付出了1.5万人伤亡的惨重代价,成功突破了俄军的外围防线。
这一行动使得俄军不得不将预备队紧急调往203高地方向,打乱了其原本的兵力部署。到了10月的第二次总攻,尽管日军仅仅向前推进了数百米,却极大地消耗了俄军的弹药,使其弹药储备减少了40%。
真正成为这场战役战略转折点的,是12月的第三次总攻。
在此次总攻前,日军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坑道作业,成功推进至距离俄军阵地仅50米处,同时配合持续的炮火压制,使得203高地守军的日均弹药配给,从开战初期的15发/人骤降至不足5发/人。
这一数据来源于俄方的《旅顺要塞防御日志》。三次总攻累计造成日军6万余人伤亡,占第三军总兵力的40%。
但最终夺取的203高地观测点意义重大,它为海军“三笠”号战列舰编队提供了精准的射击坐标。12月15日,港内的俄军“波尔塔瓦”号等3艘战列舰被精准击沉,俄军的海上力量遭到重创。
司马辽太郎在《坂上之云》中生动还原了战场细节,其中提到,俄军指挥官斯特塞尔在投降前曾无奈坦言:“历经连续150天的高强度攻防作战,要塞的炮弹储备已经耗尽了90%,第4西伯利亚军团的老兵补充率更是超过了200%,防线已然岌岌可危,即将全面崩溃。”
近年来,日本军事史学者藤冈佑纪的研究也指出,乃木希典的“逐次攻击”战术,虽然明显违背了现代战争中火力优先的原则,但在明治时期日本陆军重炮产能严重不足的现实情况下——当时国内每个月仅能生产120发280mm榴弹,通过有组织的步兵集团冲锋,巧妙地实现了“以人力换火力”的战略目标。
到1905年1月俄军投降时,其阵前遗弃的步枪弹壳数量约达1.2亿发,这一数字相当于战前旅顺要塞储备量的3倍,有力地印证了日军持续攻坚对俄军后勤体系造成的摧毁性影响。
这种堪称“尸山血海”的消耗战,从本质上讲,是日本军事工业能力难以匹配其扩张野心这一矛盾在战场上的具体体现。
它既充分暴露了萨长陆军所秉持的“精神万能论”的局限性,也不可否认地达成了迫使俄军放弃旅顺要塞的战略目的,为后续对马海战中日本舰队的顺利集结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时间窗口,对整个日俄战争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八
在20世纪初那场震撼世界的日俄战争中,旅顺战役可以说是决定整场战争胜利的关键一役。
日军在这场战役里,指挥混乱、派系分歧等问题层出不穷,内部矛盾频繁激化,犹如一艘在暴风雨中飘摇的战舰,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他们最终竟然达成了战略目标,这一结果着实令人费解,想要探寻其背后隐藏的原因,并非易事。
日本近代史学者远山茂树在其著作《明治维新史研究》中,给出了深刻的见解。
他指出,日军能取得这样的成果,深层次原因在于“萨长藩阀体制在资源约束下的动态平衡”。
日本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地缘条件犹如一把双刃剑,既赋予了它独特的海洋优势,同时也严重限制了其发展的路径。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着重强调过,资源的有限性会对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形成刚性制约,而日本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日本妄图实施大陆政策,向外扩张,就必须依靠陆军突破东北的陆上防线,开辟陆地战场;与此同时,还得依赖海军保障朝鲜海峡至辽东半岛的海上交通线,确保物资运输和军队调动的顺畅。
而这双向的战略需求,恰好与萨长两藩的势力范围完美契合:萨摩藩主导的海军牢牢掌控着制海权,在广阔的海洋上纵横捭阖。
长州藩主导的陆军则承担起陆地攻坚的重任,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表面上看,海陆军之间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比如东乡平八郎与乃木希典在战略上的分歧,常常引发激烈的争论,给人一种分崩离析的错觉。
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藩阀利益与国家目标的隐性协同”,他们在各自为藩阀争取利益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推动着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这种微妙的关系,犹如暗潮涌动下的一股合力,推动着日本在战争的浪潮中前行。
军事评论家司马辽太郎在《明治天皇》一书中,进一步揭示了萨长两派之间的复杂关系。
尽管他们在战术层面存在诸多分歧,大山岩秉持速胜论,主张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尽快结束战争。
山县有朋则倾向于消耗论,认为通过长期的消耗战,拖垮敌人,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但在“确保大陆桥头堡”这一根本目标上,两派却达成了高度一致。
他们深知,只有在大陆上站稳脚跟,日本才能实现更大的野心。这种“貌离神合”的权力结构。
追根溯源,是江户幕府瓦解后“强藩政治”的延续。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深刻剖析过,政治集团的利益整合往往会通过表面的冲突来实现深层的协作。
萨长两派正是如此,他们通过相互制衡,避免了单一军种的盲目冒进。就像当乃木希典率领的陆军在203高地陷入僵局,久攻不下时,海军面临的紧迫形势促使大本营果断启用儿玉源太郎的炮火战术,这一举措犹如在失控的列车前踩下了刹车,及时修正了纯陆军思维的局限,让战争的局势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将日本的情况与清朝和俄罗斯进行对比,日本的藩阀协作所展现出的制度优势便一目了然。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晚清时期,湘军、淮军等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矛盾错综复杂,导致中央政府的政令难以有效传达和执行,出现了“政令不出紫禁城”的尴尬局面。在辽东战场,宋庆、袁世凯等将领各自为战,互不统属,缺乏有效的协同作战能力,面对外敌入侵,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而反观日本,第三军、第二军在大山岩的统一协调下,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犹如一台精密运转的战争机器,充分发挥出了整体的力量。
俄罗斯方面,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深刻剖析了其内部的矛盾,贵族地主与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导致国家决策混乱。
旅顺要塞司令斯特塞尔采取消极防御的策略,与圣彼得堡宫廷的冒进指令背道而驰,双方的意见无法统一,最终导致了“波罗的海舰队远征”这样的军事冒险行动,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还让俄罗斯在战争中陷入了更加被动的局面。
日本的“萨长协同”本质上是对岛国自身缺陷的一种适应性进化。信夫清三郎在《日本外交史》中强调,自镰仓幕府以来,日本就形成了独特的“武家政治传统”,这种传统使得藩镇割据形态的军事集团的利益整合具备了深厚的历史惯性。
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了“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这一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海陆军部门之间的对立,但也促使萨长两派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不得不寻求“合并同类项”,以实现共同的利益。
例如,海军为了掌控旅顺的制海权,迫切需要陆军重视203高地的炮兵观测价值,因为只有占领高地,才能更准确地打击港内的俄舰。
而陆军通过艰苦的攻坚作战,成功攻克203高地后,又为海军歼灭俄舰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种在斗争中相互协作的模式,让日本在甲午、日俄战争中实现了“有限资源的最大化利用”。正如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所强调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日本的藩阀体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了一种“最不坏的选择”。
帮助日本在列强争霸的舞台上崭露头角。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对外扩张的成功,是以中国人民的巨大苦难为代价的。
据《中国近代通史》记载,日俄战争期间,东北平民伤亡超过20万人,无数家庭流离失所,家园惨遭破坏,这是日本岛国扩张主义不可掩盖的历史罪行,也是我们永远不能忘却的伤痛,时刻警示着我们要铭记历史,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后世历史学家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萨摩与长州两藩阀集团矛盾的本质。
后记
但是,萨长体制也为日本后来的军国主义暴走,埋下了隐患。
自日本战国时代起,武家专断的政治传统延续,到明治维新时期,萨长藩阀凭借在倒幕运动中的关键作用,顺势垄断军政大权。日本学者井上清在《日本军国主义》里提到,这种藩阀垄断为军国主义滋生提供了土壤。萨长军阀以军事扩张为核心,积极推动海外侵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尝到甜头,军国主义思想在国内迅速蔓延。
到了昭和天皇时代,天皇企图集权,摆脱萨长军阀集团的掣肘,于是大力拉拢、扶持少壮派军人。
这些少壮派深受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想毒害,他们鼓吹“国家至上”,主张通过战争实现日本的绝对霸权。在《大东亚战争全史》中记载,少壮派军官频繁发动军事政变,推动国家政策向战争倾斜。
“二二六事件”就是典型,他们妄图通过暴力手段实现政治变革,进一步将日本推向战争深渊。由此,昭和军阀群体逐渐形成,他们将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最终裹挟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也让日本在战争泥沼中走向灭亡的边缘。
井上清在其著作《日本军国主义》中,以犀利的笔触深刻剖析道:“萨摩与长州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源,是海洋扩张与大陆政策这两条截然不同发展路线的激烈碰撞,这种二元对立从根本上塑造了日本近代军事体制中难以修复的致命缺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