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以来,德国的人口出生率逐渐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战又损失了近一千万人口。
战后的魏玛德国陷入经济低迷,百姓负担不起生活开支,纷纷减少生育。保守派只看到表面现象,视堕胎和节育为洪水猛兽,认为这是革命党、犹太人的阴谋。
但讽刺的是,二战又造成了一千多万德意志人死亡。更讽刺的是,纳粹往德国搬运了一千多万斯拉夫伪军和奴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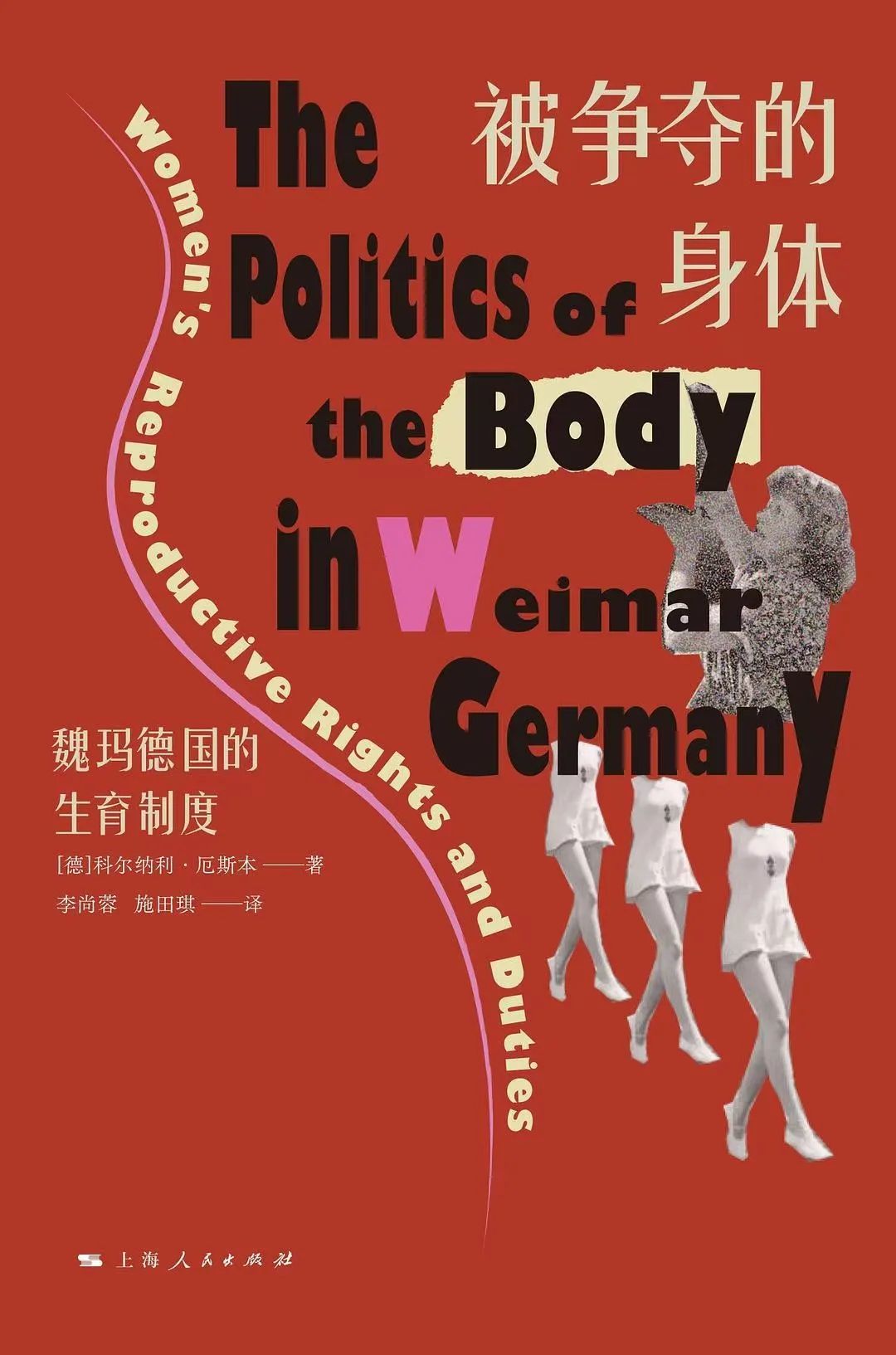
[德]科尔纳利·厄斯本,李尚蓉、施田琪 译,《被争夺的身体:魏玛德国的生育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
一、巧献毒计
在流亡德国的诸多白俄贵族里,给纳粹卖命的俄奸,不止瓦西里奇科夫公爵一个,而是多如过江之鲫,诸如比斯库普斯基,奥斯特拉尼察(温特堡),贝尔蒙德—阿瓦洛夫,塔博里茨基,萨哈罗夫……20年代初,有60万白俄侨民流亡德国,人数一度超过法国。
他们在柏林创办了200多种报刊,一边制造恐慌宣称造反的布尔什维克都是犹太-蒙古混血,犹太人故意引入有色人种搞乱欧洲,一边向德国频送秋波,以东方的土地为诱饵,煽动其进攻苏联。
纳粹党人在上台前没有与苏联产生交集,他们对斯拉夫人“生性低劣”的观念,是基于周围的白俄流亡者形成的。
早在苏俄国内战争(1917~1922年)期间,“白军”就提出将乌克兰等地送给德国的经济殖民地,换取德军和德国“自由军团”在乌克兰和拉脱维亚协助己方与苏军作战。
1919年8月,流亡报纸《呼唤》(Prizyv,俄语:Призыв)问世。塔博里茨基(Сергей Таборицкий)担任技术编辑,沙贝斯基-博克(Шабельский-Борк)起草了以俄语为主的新闻,还负责该报的连载专栏,呼吁德国和俄罗斯联合起来对抗所谓的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世界阴谋。
他们还宣称俄国贵族与本国斯拉夫刁民不同,是北欧海盗留里克的后代,与德意志人是一家。
然而,根据19世纪末的沙俄官方统计,在世袭贵族中,53%是俄罗斯族,28.6%是波兰族,5.9%是格鲁吉亚族,5.3%是鞑靼族一突厥族,3.4%是立陶宛族一拉脱维亚族,只有包括沙俄皇族在内的2%是日耳曼族。
1917年十月革命时,在105名布尔什维克代表中,俄罗斯族占了近80%,而犹太人仅占党员总数的5%~7%。俄罗斯族是俄国人数最多的民族,不仅在沙俄贵族,也在布尔什维克党里占主要地位。
沙俄骑兵将军瓦西里·比斯库普斯基(Василий Бискупский)、贝尔蒙德-阿瓦罗夫上校(Бермондт-Авалов),在德军军官赫尔曼·埃尔哈特(Hermann Ehrhardt)的带领下,参与了1920年3月的卡普政变,试图推翻魏玛共和国,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白俄在这次政变里的添乱多于帮忙。与传统右翼的结盟失败后,白俄又看中了新兴的纳粹党。从1920年到1923年,右翼组织“重建协会”与希特勒结盟,谋划推翻德国政府。
该组织全称为“东方经济政治联盟(Wirtschafts-politische Vereinigung Fur den Osten)”,致力于重建外国资本对俄国的殖民利益。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宣称:“如果我们今天谈论欧洲的新土地,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只是俄罗斯及其附属的边远国家。”
早期的纳粹意识形态结合了日耳曼民族的种族和精神优越性观念,以及白俄移民的末日阴谋论。
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主编罗森堡,长期照抄白俄侨民报纸上的阴谋论内容。他谴责魏玛德国时期的德国文化,认为它正在被自由主义摧毁,走向衰落。
后来,德国学者科尔纳利·厄斯本在《被争夺的身体:魏玛德国的生育制度》里写道,纳粹党人把女性的身体当做了与其他民族竞争的战场:“性恐慌为他们的反革命和反犹主义运动提供了可喜的素材。该党制作了传单,将少女的堕落归咎于‘革命主义对家庭的系统性破坏’。”
在《二十世纪的神话》里,罗森堡对世界历史进行了颠覆性的书写,他认为种族之间永恒的斗争是历史的核心。
他将世界文化最伟大的成就归功于拥有“北欧血统”的人们,将创造性精神与种族联系起来。“俄罗斯曾经是由维京人建立的,日耳曼元素遏制了俄罗斯草原的混乱……在20世纪之交,草原也憎恨严重日耳曼化的波罗的海人民。……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时代,鞑靼人杀害那些因身材高大、步态大胆而显得可疑的人。”
1922年,罗森堡出版《瘟疫在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的领袖、追随者和受害者》(Pest in Rußland! Der Bolschewismus, seine Häupter, Handlanger und Opfer),故意在封面画了一个满脸横肉的蒙古大光头政委。
讽刺的是,此人的长相不像当时的任何布尔什维克高层,反而肖似前沙俄莫斯科总督费利克斯·苏马罗科夫-埃尔斯顿(Феликс Феликсович Сумароков-Эльстон)。
此人是库班哥萨克首领之子,著名的“女装大佬”尤苏波夫亲王的父亲,入赘诺盖汗国的尤苏波夫家族。一战期间,他担任莫斯科总督,在1915年操纵了为期三天的反德屠杀。
罗森堡在1914~1918年都在莫斯科,不仅经目睹了1917年革命,也目睹了这场屠杀。即使他宣称俄国贵族有德意志血统,但在写书时,他还是不自觉地把“蒙古政委”描绘成了昔日莫斯科总督的形象。

《瘟疫在俄罗斯》封面

莫斯科总督费利克斯·苏马罗科夫-埃尔斯顿
二、借壳上市
约翰·史蒂芬在《满洲黑手党》里误以为,在政治经济形势恶化的影响下,德国的俄侨1923年下降到25万,1933年下降到5万。
因此俄侨对纳粹党上台后的影响不大,俄侨法西斯团体日益边缘化。他在该书序言中承认,德国档案馆里藏有关于俄国法西斯分子的有价值的资料,例如纳粹党、党卫队和东方部、外交部档案记录,他缺乏对此类德语材料的考察。。
根据美国记者迈克尔·凯洛格(Michael Kellogg)在《纳粹主义的俄罗斯之根:白俄移民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形成,1917-1945》(The Russian Roots of Nazism. White Émigrés and the Making of National Socialism, 1917–1945)里的研究,比斯库普斯基、伊拉利昂·瓦西里奇科夫、彼得·克拉斯诺夫(Пётр Краснов)和伊戈尔·萨哈罗夫(Игорь Сахаров)等沙俄贵族和旧军官也在纳粹德国的外交部、东方部和军队等部门任职。
在这些俄奸的招募下,1936年,白俄侨民已经回升到至12.5万。纳粹上台后,白俄侨民的人数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1945年,德国及其占领区的白俄伪军、苏军战俘、东方劳工已经达到1300万人之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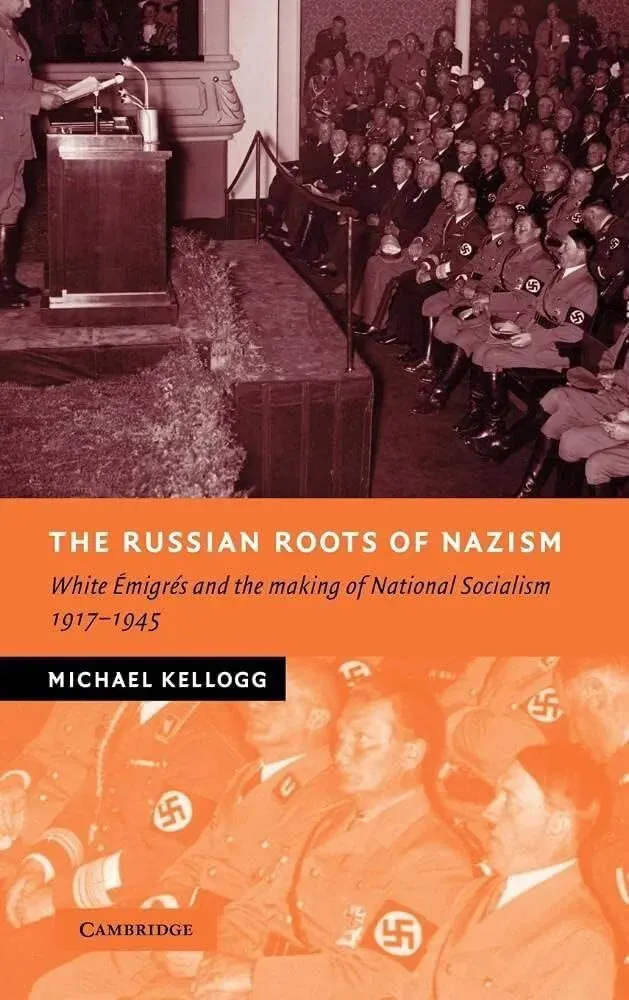
德国境内的白俄侨民由“俄罗斯驻德国委员会”(Russische Vertrauensstelle in Deutschland)监管。
希特勒任命前沙俄将军比斯库普斯基担任该组织负责人,前沙俄军官沙贝斯基·博克和塔博里茨基担任副手,三人均加入纳粹党,由盖世太保监督工作。
该组织也被称为“俄罗斯移民事务办公室”,地址位于柏林布雷特鲁大街27号(Bleibtreustraße 27)。
根据俄罗斯学者冈察连科(О. Г. Гончаренко)在《星星与万字之间的白俄侨民》(Гончаренко О. Г., Белоэмигранты между звездой и свастикой)里的研究,该组织的职责包括管理德国境内的俄罗斯侨民,为每一个15岁以上的人发放身份证明,以及对他们的政治动向进行监控,战争爆发后负责在俄侨中为德军征募翻译人员,并为盖世太保招募线人。
被招募的俄侨,通常会在德军审讯苏军战俘和游击队时担任翻译,也有很多人随德军作战或清剿游击队。
早在1923年,苏联情报部门格别乌就观察到了纳粹党和白俄复辟组织之间的路线分歧。
根据格别乌的报告,在苏俄国内战争即将结束的1922年:“他们热烈讨论人民战争的可能性,并且毫不掩饰地强调必须……以俄罗斯为基地;各种作战组织的活动正在复苏”,而希特勒“不知何故地保持沉默”。此时,伊拉利昂·瓦西里奇科夫已经崭露头角,担任德国的巴登-巴登的俄罗斯侨民联盟(Союз Рус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ов)的副主席。
这是一个支持基里尔大公称帝的俄侨右翼组织,继承自沙俄时期的右翼政党“俄罗斯人民联盟。”
1938年,基里尔大公死亡,他21岁的儿子弗拉基米尔·罗曼诺夫成为继承人。他接管了“帝国陆军和海军军团”(Корпус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рмии и флота)(KIAF)又称“正统军事联盟”。
这是一个不受纳粹控制的武装组织,创立于1924年,成员以前沙俄军官为主,最多时有1.5万人。弗拉基米尔自封为“帝国陆军和海军军团”少将,号召许多白俄流亡者加入该组织。
纳粹将他软禁在法国,将他的许多随从关进集中营。在基里尔父子的诸多亲信里,瓦西里奇科夫填补了他们留下的权力空缺,“帝国陆军和海军军团”则被编入伪军,在德国的指挥下侵略苏联。
瓦西里奇科夫没有付出成本,就截胡了基里尔大公用重金砸下的政治资源。纳粹德国外交部、最高统帅部的职位,本该属于他那有着德意志荷尔施泰因血统的“小主人”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弗拉基米尔被纳粹幽禁时,他经常越殂代疱,对柏林的白俄侨民进行“巡视”。
瓦西里奇科夫的高叔祖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的情夫,虽然出身尴尬,却遗传了一副颇为“雅利安人”的相貌。与相反,他的夫人莉迪亚出身维亚泽姆斯基家族,据称是北欧海盗留里克的后代,却有明显的亚洲特征。
其先祖是伊凡雷帝的特辖军二把手,父亲指挥阿斯特拉罕哥萨克,家传了一副蛮横暴虐的脾气,就连其他白俄侨民都对她的女儿塔蒂阿娜吐槽:“你的妈妈像愤怒的狮子一样咆哮!”。
罗森堡在《二十世纪的神话》里写道:“在俄罗斯的文明上层阶级中,始终渴望无限的扩张,有着打破一切被视为障碍的生活方式的强烈意愿。
尽管俄罗斯的生活发生了种种剧变,但混合的蒙古血统却沸腾起来,即使是在大大稀释的情况下,也吸引着人们做出一些连个人自己都难以理解的行为。”
罗森堡归咎于蒙古血统,是相当不公平的——此时金帐汗国已灭亡500年,蒙古血统比犹太血统还要稀薄,而且蒙古人在沙俄和苏联一直是被欺压的对象。
莉迪亚的女儿蜜丝为了脱亚入欧,在《柏林记忆》里吹嘘她与普鲁士元帅布吕歇尔有姻亲关系,其实中间隔了两个家族,维亚泽姆斯基只与一个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男爵结过亲。
更有甚者,布吕歇尔元帅晚年患有精神病,幻想自己怀孕,肚子里有一头大象。如果与维亚泽姆斯基家族结合,两种奇葩基因碰撞,不知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东方劳工(Ostarbeiters)约占当时德国全部劳动力的四分之一。他们当中大多数是来自东欧的斯拉夫人。
截至1944年夏末,760万平民和战俘被强行带到“大德意志帝国”领土上劳动。瓦西里奇科夫长期以红十字会的活动作为掩盖,与白俄哥萨克伪军、苏联战俘和东方劳工密切接触,计划在720事件后起事。
720计划原名为“女武神行动”(Unternehmen Walküre),该计划于1941年12月起草,旨在预防“东方劳工”和苏军战俘的起义。
所有预备役军人将占领柏林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关键军事地点,对叛乱分子采取行动。
施陶芬伯格在最高统帅部工作,自1943年调整了“瓦尔基里计划” ,以满足针对希特勒的暗杀计划的需要,将党卫军、安全局(SD)、盖世太保和纳粹党的关键人物也逮捕。
纳粹党杀死了许多720密谋者,却没有处罚白俄,因为后者所掌握的伪军势力日益壮大。1944年3月31日,克拉斯诺夫成为哥萨克部队总指挥部(GUKV)的负责人。
哥萨克兵团主要负责从苏联领土招募哥萨克人,还把原本在德国国防军(党卫军)部队服役的白俄哥萨克转移到这支部队。哥萨克部队总指挥部负责培训军官干部,以及在忠诚于德国占领当局的精神下对青年、军官和士兵进行教育。
同年,苏联叛将安德烈·弗拉索夫(Андрей Власов)于1944年组建了另一支伪军“俄罗斯解放军”,约有10万人,以苏联战俘和白俄流亡者为主。沙俄军官伊戈尔·萨哈罗夫担任他的作战副官。
从1917年以后,瓦西里奇科夫和莉迪亚在红十字会里没有正式职位。能够打着它的名义活动,是靠着纳粹的许可。
据苏军战俘说,红十字会的护士也经常戴着纳粹袖标招摇过市——说的是他们的女儿蜜丝。在整个战争期间,由于饥饿、疾病和处决,大约有330万名苏联战俘被杀害,“不食嗟来之食”,对于那些苏军来说不现实。但拿着一个面包引诱,让他们去当伪军,这绝不是“慈善”。
《柏林记忆》里故作同情地写道:“这批可怜人(哥萨克伪军),被夹在交战两方中间,进退不得”,下文又原形毕露:
“哥萨克人一直是最强烈反苏的民族,……他们带着全家,甚至全村,一起投效德国……在南斯拉夫境内进行反游击战,多方奏捷。到了大战结束前最后几周,他们一路战斗,穿越奥地利,最后总计约六万人向英军投降。
结果英国比照对待弗拉索夫将军所率领之“俄罗斯解放军”的方式,强行将他们交到苏联手中。
许多人(包括妇孺)因此自杀,高级将领皆被吊死,低级军官则被枪决,其他人被送往古拉格,生还者极少。”
直到七八十年代,蜜丝和乔治姐弟还向西方强调这些哥萨克“强烈反苏”,“多方奏捷”的特殊“价值”。这些哥萨克在南斯拉夫残杀的,难道不是他们的斯拉夫兄弟吗?

“这是我的手足兄弟,挚爱亲朋啊,要杀他,得加钱!”-电影《绣春刀》截图
在弗拉索夫的带领下,伪军“俄罗斯解放军”同样在东欧犯下了一系列罪行。在1945年布拉格起义期间,德意志族居民也沦为他们的种族仇杀对象。
捷克作家鲁道夫·斯特罗宾格(Rudolf Ströbinger)和剧作家帕维尔·科豪特 (Pavel Kohout)提及:“关于德国士兵和平民遭受可怕虐待的报告大批大批地传来。最可怕的画面是德国人耷拉着脑袋挂在路灯上,他们被点燃了。”
英国人自然不敢接收这样的军队,唯恐引火烧身。
1945年,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军服役期间,在普鲁士曾经见过一个被俘的伪军被苏军军官当众鞭挞致死。在鞭挞过程中,这名伪军十分悔恨,多次说“对不起”,但已铸成大错,无法挽回。


瓦西里奇科夫的儿子乔治与苏联“老左”柯切托夫
懦弱、残忍而又自大的俄罗斯贵族从来都不会堂堂正正地战斗。他们被蒙古人击败,被克里米亚鞑靼人击败,被德国人击败,被日本人,被布尔什维克击败。任何人都可以做俄罗斯贵族的主人。
他们从来不懂得什么是荣誉,什么是忠诚。当你的大军取得胜利,他们就会望风归附,请求你带领他们烧杀抢掠。当你失败了,他们就会从背后捅刀子。
早在1939年,瓦西里奇科夫就两头下注,向苏联出卖了立陶宛,克拉斯诺夫和洛扎耶夫斯基在战后也向斯大林卑躬屈膝,极尽谄媚之能。
德国的保守主义者,忽略了两个问题:1.如果德国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可以通过移民政策决定外来人口的比例,但如果沦为战败国,就要听从他人安排。2.文明与否,不是血缘决定,而是制度与文化决定的。
无论犹太人和蒙古人怎样,谁该做德国人——这个问题不该由这些在德国做俄奸的俄罗斯贵族决定。他们蛀空了沙俄,又蛀空了德国——他们才是自己口中的“东方盲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