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自杀是他者的罪恶
选自:《议程》
《议程》的两个片段
[法] 埃里克·维亚尔孟湄 译
面具 LES MASQUES
我们可以这样一个挨一个地去靠近那二十四位走进国会大厦的先生:紧挨到他们的领口和他们熨贴的领带结,盯住他们小胡子下嚅动的嘴,在他们西服上衣的虎皮纹路间遐想,潜入他们目光愁闷的眼睛,进入那瞳仁——它们像刺人的黄色山金车花,从那里,我们总是找到一扇同样的小门;我们去拽一下门铃的绳子,就会重新回到过去的时光,在那里我们会看到他们丰功伟绩的单调叙述,都是一样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操作、美好婚姻、令人生疑的种种行动。
在这个2月20日,亚当·冯·欧宝 (Adam von Opel)的儿子威廉已经永远地刷去了渗进指甲缝的油污,收起了自行车,遗忘了缝纫机,然而他身上依旧带有那么一颗子粒,它凝集着这门望族的全部传奇。六十二岁的他,很轻地嗽了一下嗓子,看看腕上的手表,嘴唇紧闭,眼睛向四下环视。亚尔马·查赫特(Hjalmar Schacht)活儿干得漂亮(此后他很快被任命为德国国家银行行长和政府经济部长)。请看在会议桌前入座的人士:古斯塔夫·克虏伯(Gustav Krupp),阿尔伯特·沃格勒(Albert Vögler),君特·匡特(Günther Quandt),弗里德里希·弗雷克(Friedrich Flick),恩斯特·腾格尔曼(Ernst Tengelmann),弗里茨·施普林格鲁姆(Fritz Springorum),奥古斯特·罗斯特尔格(August Rosterg),恩斯特·勃朗迪(Ernst Brandi),卡尔·布伦(Karl Büren),君特·霍伊贝勒(Günther Heubel),乔治·冯·施尼茨勒(Georg von Schnitzler),小胡戈·斯廷内斯(Hugo Stinnes Jr),爱德华·舒尔特(Eduard Schulte),路德维希·冯·温特菲尔德(Ludwig von Winterfeld),沃尔夫-迪特里希·冯·维茨莱本(Wolf-Dietrich von Witzleben),沃尔夫冈·罗伊特(Wolfgang Reuter),奥古斯特·迪恩(August Diehn),埃里克·菲克勒(Erich Fickler),汉斯·冯·卢文斯汀·楚·卢文斯汀(Hans von Loewenstein zu Loewenstein),路德维希·格劳尔特(Ludwig Grauert),库尔特·施密特(Kurt Schmitt),奥古斯特·冯·芬克(August von Finck),还有施泰因博士(Dr Stein)。眼前乃工业界、金融界之翘楚。此时此刻,人人沉默不语,乖顺谦逊,已经等待近二十分钟,他们面有怠倦,椅背的横梁腾起烟气,微刺他们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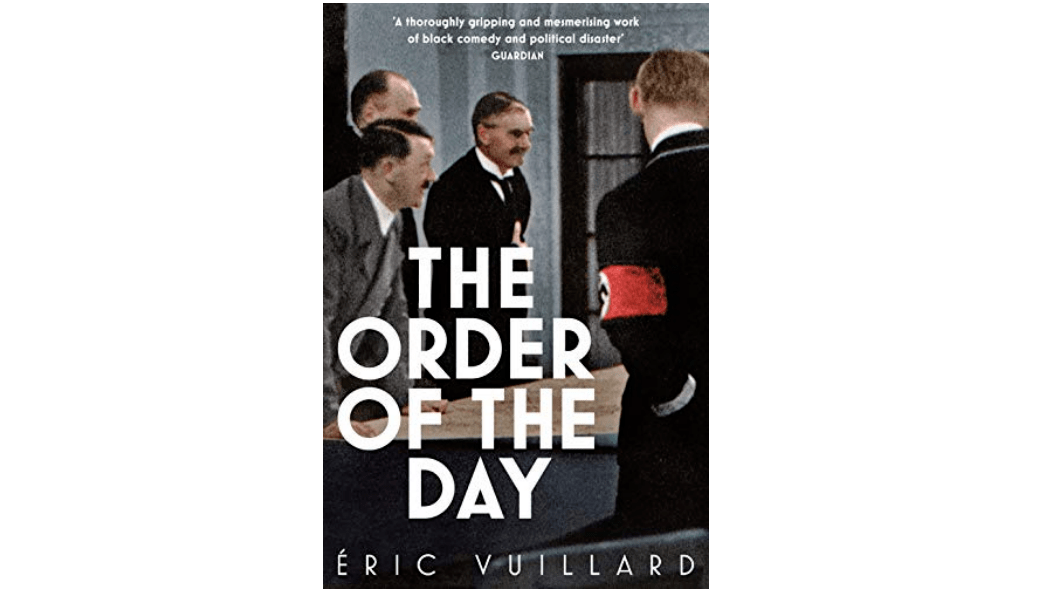
几条身影在一面镜子跟前停住,整理领带结,姿势恭敬,那里是小客厅,有人在宽衣。帕拉第奥(Palladio)在他的《建筑四书》( The Four Books onArchitecture ) 中,把沙龙大致定义为接待宾客的房间,那是展现我们生命笑剧的舞台;在著名的戈迪·马林维尔尼宫(Villa Godi Malinverni)里,有座奥林巴斯厅,裸体的众神在看似颓垣败壁的场景中嬉戏,还有一座维纳斯厅,墙上一个顽童和他的侍从正从画上的一座假门逃跑。走过这两座厅,到达中央大厅,可以看到一道铭言在大门上方,那是一句祈祷词的结尾——“救我们脱离凶恶”。但是在国会主席的宫殿里,在此刻的小型接见会上,要寻找这样一段铭文当然是徒劳;它不在这一天的议事日程中。
高大的天花板下,又是几分钟缓慢过去。人们相互交换微笑。人们打开皮质文件夹。查赫特不时地抬一抬他精致的眼镜,轻搓一下鼻子,伸出舌头在嘴唇边抿一下。客人们都乖乖坐着,把他们鳌虾般的小眼睛朝着大门望去。人们小声说话,中间有人打哈欠。一块手绢被打开,寂静中鼻孔吹出小号声,人们再次正一下衣襟,耐心等待会议开始。其实人们已经熟悉这些了,所有人都身负某些行政或者监督顾问的职责,所有人都是某某雇主协会的成员。且不说这个严肃郁闷的家长制背后那些阴森不堪的家庭会议。
坐在第一排的古斯塔夫·克虏伯用手套轻触了一下自己红润的脸,掏出手绢儿虔诚地咳了一下,他感冒了。随着年龄增长,他薄薄的嘴唇开始显出不很好看的朝下弯的月牙形状。他面带愁容和不安,机械地在手指间转动着一枚漂亮的金指环,陷在他那团希望与算计搅在一起的浓雾里——也许,对于他,这两个词只有一个简单的意义,好像它们已经缓慢地相互磁化到一起。
突然,几扇门发出吱呀响声,地板被踩出咯叽声;有人在前厅说话。二十四只“蜥蜴”立即坐到“后爪”上,个个脊梁笔直。亚尔马·查赫特把唾沫一口咽了下去,古斯塔夫正了一下他的单片眼镜。能听见两扇门背后压低声音的对话,接着,又一片声响。终于,德国国会主席微笑着走了进来:赫尔曼·戈林 (Hermann Göring)。这或许会让我们惊讶,对与会者来说却远非如此,说到底,是司空见惯,已成寻常。在生意人的日子里,拥护谁的斗争算不得什么。政界人物与工业家习惯于你来我往。
戈林环绕会议桌走了一圈,跟每个人都寒暄一两句,温厚的手握住朝他伸过来的每一只手。不过,德国国会主席不仅仅是接见诸位。他说了几句欢迎词,然后立刻将话头转到即将到来的选举,日期是5月3日。二十四只“斯芬克斯”认真听讲。即将开始的选举将具有决定性意义,德国国会主席宣称,制度的不稳定到了该结束的时刻;经济活跃需要安宁和坚定。二十四位先生虔敬地点头。吊灯的电光蜡烛熠熠闪烁,画在天花板上的硕大太阳比方才更见辉煌。如果纳粹党赢得大多数选票,戈林接下去说,这次选举对今后十年,甚至——他笑着补充——对今后的一百年,都将是最后的选举。
座位上传出一片赞许声。同一时刻,厅门发出响声,德国新总理终于走进大客厅。与会者中从未见过总理的人此时很好奇看到他本人。希特勒面带微笑,神情轻松,根本不同于人们的想象,他和蔼可亲,是的,他甚至让人愉快,远远比人们以为的要可爱得多。他对每个人都说了一句感谢的话,给了一个有力的握手。介绍过后,大家都回到舒适的座椅上。克虏伯坐在第一排,一只手指神经质地揪扯自己的小胡子;他背后是法本公司 (IG Farben)的两位领导人和奥古斯特·冯·芬克,再旁边,匡特和另外几个人貌似斯文地两腿交叉而坐。有人发出一声很深的咳嗽,一只钢笔帽发出了极轻微的声响。之后,一片寂静。

来自:Quatre Sans Quatre
他们在那里洗耳恭听。讲话内容的实质可以这样概括:我们要结束软弱的制度,远离共产主义的威胁,取消工会,要让每一个老板都成为自己企业的“元首”。报告持续了半小时。希特勒讲完话,古斯塔夫站起身,朝前迈出一步,代表在座的所有人向希特勒表示感谢,他终于给众人厘清了政治形势。总理迅速地围着会议桌转了一圈,然后就离开了客厅。人们都向他致意,彬彬有礼。老工业家们看上去都放松下来。希特勒离开后,戈林又开始讲话,他再次竭力重申他的看法,然后又提到即将到来的3月5日选举。这是走出当下困境的唯一机会。但是,要进行选举,就需要钱;纳粹党已经没钱了,而选举正在逼近。这时,亚尔马·查赫特站起身,向所有到会者微笑,并发出号召:“先生们,现在请捐款吧!”
这声招呼当然带着一点单枪匹马的感觉,然而对这些人来说,这绝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他们习惯了贿赂和桌下交易。行贿是大公司预算中不能压缩的一项,这一项拥有好几个名称:游说、年赏、政党支持。大多数受邀者当即每人捐出了几十万马克,古斯塔夫·克虏伯捐了一百万,乔治·冯·施尼茨勒四十万,就这样,纳粹党收获了一个圆满数字。1933年2月20日的会议,让我们看到雇主们在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刻——面对纳粹,他们做出前所未有的妥协,不过这对于克虏伯们、欧宝们、西门子们来说,不过是企业经营中一个平常的片段,一次寻常的捐款。他们所有人都在纳粹制度后存活下来,并且在日后仍旧根据自己的实力为不同政党提供资助。
但是为了更好地理解2月20日的会议,抓住其中永久性的实质,我们应当从现在起以这些先生的姓氏来称呼他们每个人。他们不再叫君特·匡特、威廉·冯·欧宝、古斯塔夫·克虏伯、奥古斯特·冯·芬克,在1933年2月20日那个傍晚,在德国国会大厦主席宫里,应该用另外的名字称呼他们。因为君特·匡特是一个匿名,他隐匿的东西完全不同于那个唇上留着小胡须笑容可掬端然而坐的胖家伙。在他身后,有一个截然不同的威严身躯,一个卫士的影子,寒冷,难以猜透,如一尊石像。是的,匡特的脸凸显出他的威严、强势、残忍、毫无个性,这使他像一副面具生硬无情,这副面具比他自己的皮肤更适合他,人们可以从那上面猜出他的企业:AG蓄电池,后来是瓦尔塔牌 (Varta)电池,这个品牌我们都知道。看来法人们都拥有自己的天神阿瓦达,如同古代的众神,他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各种形式现身,与其他神聚集到一起。
这就是匡特家族的真名,他们的造物主之名。这样说是因为,君特,他和你们和我是一样的,只是一堆血肉和骨头,但是在他之后有他的儿子们,儿子们之后有儿子们的儿子们,他们都会继续坐在“王位”上。人的血肉和骨头会在地下腐烂,而“王位”仍将延续。那二十四个人,不像我们以为的就叫身份证上的名字,他们不叫施尼茨勒,不叫维茨莱本,不叫施密特,不叫芬克,不叫罗斯特尔格,不叫霍伊贝勒。他们叫巴斯夫 (BASF)、拜耳(Bayer)、爱克发(Agfa)、欧宝(Opel)、法本、西门子(Siemens)、安联(Allianz)、德律风根(Telefunken)。这些名字,我们都知道,我们甚至非常熟悉它们。它们就在那里,在我们之间,在我们当中。它们是我们的汽车,我们的洗衣机,我们的闹钟-收音机,我们的房屋保险,我们手表的电池。它们在,无处不在,以物的形式。我们的日常也是它们的日常。它们医治我们,制作服装给我们,提供光明为我们,在全世界的公路上运送我们,温柔地哄着我们。2月20日在德国国会大厦主席宫里的那二十四个人,不过是这一切的代理人,是大工业的教士;是普塔的司铎。他们站在那里面无表情,如同地狱门口的二十四台计算器。

The Secret Meeting of 20 February 1933 ©Der Kamerad
死者 LES MORTS
为把德奥合并做实,那些人还搞了一场公民投票。最后剩下的反对派被逮捕了。神甫们在布道台上呼吁为纳粹投票,教堂用纳粹的十字标装饰自己。连旧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也呼吁投赞成票。奥地利人以99.75%的选票支持自己的国家并入帝国。正当本书开始时刻出现的二十四人,那些德国大工业的神甫,一起研究如何切割奥地利的时候,希特勒在该国做了一圈访问,这被誉为凯旋之旅,每到一地都有集会,到处受欢呼,令人不可思议。
然而,就在德奥合并之前,在一周内曾经有一千七百人自杀。很快,在报纸上公布的自杀事件将变成了一项抵抗行动。仍旧有若干记者斗胆写出“突然死亡”这样的字眼;事后的报复使这些人很快不再出声。有人试图寻找其他惯常说法,但是没有找到。因此,自杀的人数是未知数字,自杀者的名字也不为人知。在德奥合并的第二天,在《新自由报》 ( Neue Freie Presse ) 上还能读到四条讣告:“3月12日,上午,阿尔玛·比罗女士,四十岁,官员,用剃须刀割腕,然后打开煤气。同一时间,作家卡尔·施莱辛格,四十九岁,向自己的太阳穴开枪。主妇,埃莱娜·库赫纳,六十九岁,自杀。下午,莱奥保罗·比安,官员,三十六岁,从窗户跳下。原因不明。”这最后几个字充满耻辱。因为在3月13日,没有人可以对他们的动因视而不见。没有人。人们不能谈论那些动因,但是它们都来自同一个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
阿尔玛,卡尔,莱奥保罗或者埃莱娜,他们也许从自己家的窗口望见了那些被拖到街上的犹太人。只消远远地瞥见那些被剃了光头的人,他们就能明白。只消看到那个男人的枕骨上被人画了T型十字架,而许士尼格总理一小时前在自己的西服衬里上也别着它。甚至在这些事情之前,只消有人告诉他们,只消他们自己猜出来,自己估计到,想象到,只消他们看到有些人脸上现出微笑,他们就会明白。
那些犹太人被叫喊的人群围观,蜷缩着身体,蹲在地上,被迫在看热闹的行人目光下打扫街道,其实,那个早上埃莱娜是不是已经看到或者没有看到这一切,已经不重要。还有那些逼迫犹太人吃草的卑鄙场面,她有没有在一旁看到,也不重要。她的死亡只是传译了她心中的拒绝,她拒绝接受巨大的不幸和可憎的现实,拒绝接受在她眼前赤裸裸展开的凶杀世界带给她的厌恶。因为说到底,罪恶已经在那里,在那些小旗子上,在那些年轻姑娘的微笑里,在整个充满邪恶的春天里。她听到那些笑声,那些毫不在乎的宣泄,埃莱娜已经感觉到那里面的憎恨和享受。她已经从那里面隐约看到了,在做出这个令人战栗的决绝行为的一刻,她看到了那后面有数千个身影、面孔,数百万苦役犯。她在令人恐怖的万众欢腾中,已经猜到了毛特豪森 (Mauthausen)集中营的将来。她已经看见了自己的死亡。在1938年3月12日维也纳姑娘们的微笑中,在人群的喊叫声中,在勿忘草清新的气味里,在诡异的喜悦的心里,在所有那些狂热的心里,她已经感觉到黑色的悲哀。

On 10 May 1933, students burn ‘un-German’ books on Opernplatz in Berlin. In other univerisity cities, students also burn books by writers like Karl Marx, Sigmund Freud and Erich Maria Remarque. Collection: NIOD, Amsterdam (Beeldbank WO2) / photographer unknown
人们抛撒着彩色纸带卷,跳着各种花样的舞蹈,挥舞着一面面小彩旗。那些因为热情而疯狂的姑娘,她们后来怎么样了?她们的微笑呢?她们的无忧无虑呢?那一天她们的面容那么真诚,那么快乐!1938年3月的那场万众欢呼后来如何了?如果在今天,她们当中有人在屏幕上认出自己,她会想什么?自从世界诞生以来,人的真实思想始终是秘密。说话到了字词末尾便不再出声,屏住了呼吸,正是在那里有我们的思想。那下面,生命流淌,如树木的汁液,缓慢,藏于地下。现在,她的嘴唇边已生出皱纹,眼皮变得微红,喉咙不再发声,目光摇晃在眼前的景物间;电视机屏幕放出她昔日的影像,女护士在她身边忙碌,从昔日的影像到跟前的酸奶,那位护士与那个战争年代已经距离遥远,一代代人更迭来往,如同黑夜里轮换值班的哨兵;走过的青春、水果的味道、从身体深处涌上来的让人喘不上气的苦水,怎样把它们和恐怖区分开?我不知道。在她居住的退休之家,在淡淡的乙醚和碘酒气味中,在她如小鸟般的脆弱中,皮肤皱皱巴巴已成老小孩的妇人在电视机冰冷的长方形屏幕上认出了自己,她过去可是生气勃勃,她经历了战后的废墟,美军或苏军的占领,现在她的拖鞋在房间的塑料地板上吱吱作响,护士打开门,她微温的布满老斑的手正在慢慢地从藤椅扶手滑下,她会不会有时叹一口气,透过那股消毒水气味找出那些难以忍受的往日回忆?阿尔玛·比罗,卡尔·施莱辛格,利奥波德·比安,还有埃莱娜·库纳尔,他们都没能活这么长久。1938年3月12日,利奥波德从窗户跳下去之前,已经多少次看到了真相,多少次被耻辱折磨。他不也是奥地利人么?他不也是好几年以来已经承受了国家天主教党令人发笑的戏谑吗?那天早上,两个纳粹分子按响他的门铃,这个年轻人的面容瞬间苍老。一段时间以来,他在寻找能够摆脱官方和那些暴力的新词语;但是他找不到。他整日在街上游荡,满心害怕,怕碰见一个恶意的邻居,怕碰见一个看到他便马上把目光移开的旧时同事。他热爱的生活不复存在。什么都没有剩下:给他快乐的工作中的一丝不苟,简单而匆匆的午餐——站在一座老楼房底下一边啃着东西一边看着过往行人。一切都已经被摧毁。3月12日那个早晨,门铃响了,思绪把他包围在淡淡雾里,有一刻,他听到自己内心那个细小的声音,它总是从久久遭受毒害的灵魂中逃脱出来;于是他打开窗户纵身跳下。
瓦尔特·本雅明曾经写了一封信给玛格丽特·施特芬 (Margarete Steffin),语调中带着愤怒的讽刺,时间的推移和战后揭露的事实让我们在今天感受到那种不可承受的被压迫。他说那个时期给维也纳犹太人的煤气供应突然中断了,那些人的消费给煤气公司带来损失。因为这些人是最大的消费者,但是他们不交煤气费,本雅明做了这样的补充。本雅明的信在这里做了一个奇怪的转弯。我们不敢肯定是不是读懂了。我们对此迟疑。它的意义在树枝间游移,在苍白的天空里。然后它明朗起来,突然在莫名之地形成了一片小水洼,饱含意义,成为所有时间里最为疯狂最为悲伤的一片水洼。事实是:奥地利煤气公司拒绝给犹太人供应煤气,因为他们用煤气自杀,留下了没人付钱的煤气单。我问自己这是真的吗?那个时代已经用神经失常的实用主义手段制造了那么多恐怖!或者说这只是针对纳粹的一个笑话?有人在灾难的烛光下发明了这个可怕的笑话?然而,它到底是一个痛苦至极的笑话还是一个事实,这已经不重要;幽默朝着如此沉重的黑暗低下头,因为它在诉说真相。
在这样的敌意下,所有的事情都遗失了自己的名字。那些事情离我们远去。人们不能再谈论自杀。阿尔玛·比罗不是自杀。卡尔·施莱辛格不是自杀。埃莱娜·库纳尔也不是自杀。他们当中没有人自杀。他们的死亡无法跟那些有关他们苦难的神秘叙述相认同。人们甚至不能说他们选择了有尊严地去死。不。不是个人隐秘的绝望把他们毁灭。他们的痛苦是一个群体的东西。而他们的自杀是他者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