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时期企业的行动自由
来源: 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
原作者: Peter Hayes教授 译者: 花亦心落(QQ心情无语)
近年来,克里斯托夫·布赫海姆(Christoph Buchheim)与其前学生约纳斯·谢尔纳(Jonas Scherner)提出的第三帝国政商关系重新诠释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一论点通过以下形式呈现:2006年发表于多家权威期刊的系列论文;二人为近期出版的会议论文集《纳粹时期的德国工业》(German Industry in the Nazi Period)撰写的专题文章;以及谢尔纳博士的新著。尽管其论证大量吸纳了现有研究中已被公认且无争议的成果(但往往未充分注明首创者甚至未提及已有相关研究)[1],其核心论述仍存在显著问题:关键论点或为攻击“稻草人”,或仅重申学界共识;其余部分则以简单化、误导性的方式切割当前研究现状。
布赫海姆和谢尔纳诠释的核心命题如下:
1. 纳粹国家为实现自给自足与重整军备对德国企业实施监管,但其调控缺乏系统性,且从未建立类似中央计划经济的体制。
2. 因纳粹政权普遍尊重私有财产权与契约自由,其鲜少强制企业服务于国家目标,而是通过提供系列激励措施(inducements),企业可自由选择接受或拒绝且无需承担不利后果,促使企业达成政权生产目标。
3. 在此背景下,纳粹德国私营企业在投资决策与生产战略上仍保有高度自主权,其策略持续反映管理者对长期商业前景的评估。
上述命题的问题在于实在是太片面之辞了。第一点利用纳粹经济众所周知的即兴性与缺乏中央计划性特征,而转移了以下事实的注意力:1933-1934年纳粹贸易政策引发的干预螺旋,至1938年已发展成针对所有生产要素的全面、强制性的国家配给与分配制度[2]。该制度在战争期间日趋严苛,并于1942年后近乎无懈可击。
第二点正确指出纳粹政权出于意识形态与现实考量偏好“胡萝卜”而非“大棒”政策,但严重错误地否认了该偏好的显著例外事件所营造的威慑效应:包括1933年强制出售容克斯飞机制造公司、1934年征募私营企业注资组建褐煤汽油股份公司(Brabag)、1937年以建立赫尔曼·戈林工厂为名从德国重工业近乎没收萨尔茨吉特(Salzgitter)铁矿区,更遑论战争期间大量企业高管被撤职(如古特霍夫农冶炼厂(Gutehoffnungshütte)的保罗·罗伊施(Paul Reusch)、航空业的威利·梅塞施密特(Willy Messerschmitt)与恩斯特·亨克尔(Ernst Heinkel)、宝马的弗朗茨·约瑟夫·博普(Franz Josef Bopp))对企业决策的影响。
第三点正确指出许多企业领袖反复设想(实为渴望)回归前纳粹自由市场式的经济前景,因而试图维持传统核心业务。但布赫海姆与谢尔纳均夸大大多数大型企业在维持常态经营方面取得的有限成功,并低估1937-1942年关键时期众多高管依据政党路线大幅调整商业前景评估的广泛程度。

而且,布赫海姆与谢尔纳将第三帝国史学研究中的“唯意志论转向”引入该时期政商关系领域。这一由尼尔·格雷戈尔精辟描述与批判的思潮[3],强调德国人“自愿、自由选择”参与纳粹政府政策的诠释倾向。通过一方面强调纳粹政权对私有财产权与契约自由的“尊重”,另一方面将企业界对纳粹举措的评估简化为遵循市场份额关注、短期与长期盈利能力等传统资本主义决策标准,二人描绘出近乎“正常”的资本主义经济图景:政商谈判基于相对平等且熟悉的框架进行,企业仅受到轻微限制的行动自由。总体而言,他们认为企业决策是企业家基于自身意愿、利益考量与优先级作出的“无约束”选择,如果企业与纳粹政权合作,那就主要出于自主意志。
这一重新诠释与过去三十年间纳粹政权企业研究领域形成的更为精细的共识观点大相径庭[4]。
该共识将纳粹经济视为市场机制与国家指令的混合体,是激励与命令、奖赏与报复、机遇与阻碍的复合系统。在这种“胡萝卜加大棒”或“斯金纳箱(Skinner Box)经济”中,企业微观经济决策日益被导向政权期望的方向,其驱动力来自双重因素的交互作用,分别是“正向激励”(政府资金支持与国家担保特定商品的利润率)和“反向约束”(持续收紧的官方管控、违规重罚、政府强制可能性,以及拒绝合作可能为竞争者创造机会的风险 )
换而言之,第三帝国既束缚又刺激了利润动机。一套复杂且权宜的正负强化机制影响着大多数企业的生产与投资决策,且这些决策逐年更深度地受制于政权的宏观经济优先事项。布赫海姆与谢尔纳实质上试图剥离该叙事中的反向约束维度。在他们笔下,恐惧与强制在限制纳粹时期企业生产决策自由方面几无作用;甚至宏观经济调控也罕有实质影响。
这种对第三帝国企业行动自由的新诠释,在我看来是分析层面的倒退。尽管布赫海姆与谢尔纳的诠释或许能解释中小型企业的决策逻辑,但其严重误判了纳粹统治下德国大型企业的真实处境与思维模式。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述所有反对意见及佐证,故将聚焦于其论述中两个关键缺失,正是这些缺失使其论点根基动摇。
首先,如同整体唯意志论转向的缺陷,布赫海姆与谢尔纳的论述几乎完全无视纳粹德国的政治背景——该政权持续公开威胁任何未按其定义服务“国家利益”的个人或实体,且保留极大专断惩处空间。例如,重工业界对1937年强占铁矿的抵抗,最终因戈林直白威胁将依据《经济破坏防治法》起诉反对者[5]而瓦解。
诚然,在需要借助企业能力与专业知识的体系中,政权通常展现灵活性:通过提供融资方案降低企业承接政府订单的风险,仅在Plan A失败的关键领域(如赫尔曼·戈林工厂与大众汽车公司)才诉诸强占或成立国有竞争者。据我所知,学界权威对此并无异议。但学者们同时强调:这些Plan B的实施对企业界产生深远震慑效应——尤其当政府发言人反复将其宣称为可复制的先例时。

第二,布赫海姆与谢尔纳的概括性结论建立在对政企关系单一维度的选择性审视之上,即仅关注企业对纳粹政府要求实施项目的反应。然而,第三帝国时期政企关系性质的另一个同等重要指标,涉及企业自主提出但遭国家阻止的项目。当企业试图基于纯商业考量(非国家利益考量)推进发展战略时,往往会发现当局成为坚定而有效的阻碍。布赫海姆与舍尔纳多次暗示,企业于1930年代积累的大量储备资金可自由支配,因此公司能在无严重干预下实施自主发展战略。近年大量企业研究表明这种论断完全错误,根源在于当局对原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及劳动力的管控[6]。
事实上,这些积累储备的规模本身即反映出企业决策所受的约束。由于存在股息上限、企业利润税率从1935年的20%逐年递增5%至1942年的55%,且储备资金利息亦被固定,若无视企业被禁止的自主行为,便无法理解其为何愿意遵从国家指令。
我的首要异议主要针对第三帝国时期德国企业高管的心态或工作预设。布赫海姆认为,这类人从未认真对待纳粹零星的国有化或社会化工业威胁,因为此类举措对政权造成的成本必然超过收益[7]。谢尔纳补充指出,自1936-1937年“四年计划”启动后,政权对企业的此类威慑手段已极少使用[8]。两位学者强调,因此大多数企业仍基于传统商业考量制定生产战略,包括避免产能过剩与维护核心市场,以确保长期竞争力。此论点的主要问题在于:此类言辞威胁绝非零星偶发,而是持续存在(尽管在1937-1938年与1940-1941年等时期达到数次高潮)。在关于IG法本公司的著作中,我列举了众多例证,包括希特勒于1937年9月的公开声明:“若私营企业未贯彻四年计划,国家将全面接管工商业”;以及国务秘书布林克曼(Brinkmann)在1938年10月保险与银行高管会议上的警告,切勿“低估国家在工商业无法充分产出或创新时实施全面管控的可能性”[9]。在关于德固赛(Degussa)的著作中,我援引了该公司管理委员会主席赫尔曼·施洛瑟(Hermann Schlosser)于1940年7月(即德国西线大捷后)对其同僚的告诫:
无论正当与否,若私营经济基础的扩张主动性及速度被视为不足,则不仅计划性体制、乃至国家强制体系的风险都将加剧……若工商业未能充分把握机遇,赫尔曼·戈林工厂所体现的趋向必将再度强化[10]。
同样地,杰拉尔德·费尔德曼(Gerald Feldman)关于安联保险(Allianz)的著作充分记录了纳粹圈内反复出现的保险业国有化接管主张对该企业高管造成的心理威慑。此外,研究纳粹时期商业银行的团队首部出版著作记载了国家银行副行长库尔特·兰格于1941年1月的演讲,该演讲罗列股份制银行(joint stock banks)执行政府政策的所谓不足,并尖锐提醒其管理者:防范潜在国有化的最佳解药是“对民社主义经济计划采取正确态度”[11]。亨利·特纳(Henry Turner)关于欧宝汽车(Opel AG)的著作援引该公司1936年中旬向美国母公司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报告,称欧宝面临“隐性没收威胁”;并指出美国管理层于1939年秋退出董事会,同意生产德国轰炸机零部件仅为避免政府授权容克飞机公司接管[12]。

布赫海姆与谢尔纳似乎对这些大量言论无动于衷。两位学者的分析均未提及上述案例,亦未涉及德国实业家(尤其是1937-1942年间)的诸多书面陈述,他们必须证明私营企业能达成何种成就,以免国家采取替代手段。
在关于法本公司的著作中,我还节录了另一份高度相关的文件,显然这份文件也未能引起布赫海姆或谢尔纳的注意。这份未署名的备忘录记录了1938年10月20日的会议,当时政府与鲁尔主要煤炭生产商正就产量及分配问题发生冲突。与会者包括普鲁萨克公司(Preussag)、古特霍夫农冶炼厂(Gutehoffnungshütte)、奥托·沃尔夫(Otto Wolff)新基尔克钢铁厂(Neuenkircher Eisenwerk)的四名高管,以及联合钢铁公司(Vereinigte Stahlwerke)主席恩斯特·彭斯根(Ernst Poensgen)、国家经济院(Reichswirtschaftskammer)院长阿尔伯特·皮茨施(Albert Pietzsch)、曼内斯曼(Mannesmann)主席兼国家工业总会(Reichsgruppe Industrie)负责人威廉·藏根(Wilhelm Zangen)。
会议核心议程是讨论藏根与赫尔曼·戈林的近期会晤。戈林要求德国工业界在未来一年将出口收入增加10亿帝国马克,以确保国家有足够外汇购买战争准备所需关键物资。藏根如此总结戈林的观点:
他(戈林)认为德国工商业界已与他同样认识到局势的严峻性。若目标仍无法达成,他将别无选择,只能任命国家专员指挥经济,并赋予其全权——包括接管特定产业部门,只要他认为这些部门无法履行国家之要求。
备忘录作者(疑似彭斯根)在这份六页文件的结尾写道:
我也认为当前我们正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若给国家以口实指责我们表现不力,征用将不可避免……我完全能预见,届时煤矿业将自上而下被命令实行社会化(socialization)……工商业、尤其是采矿业,从未面临今日这般危机[13]。
这些绝非自信认为政权会妥协的企业高管之言。
布赫海姆与谢尔纳关于“政权对私营企业的言辞恫吓因未付诸实践而未影响企业领袖”的论断显然不实。1939年,保罗·瓦尔特(Paul Walter)被任命为国家煤炭专员,有权强制规定产量与分配。其无能很快成为促使工业领袖与政权合作的强力诱因,如同此前的社会化威胁般奏效,两年后他被赫尔曼·戈林工厂负责人保罗·普莱格(Paul Pleiger)排挤[14]。但关键在于:政权确实实施了其威胁,且方式足以令实业家担忧重演。即便缺乏此类反例,布赫海姆/谢尔纳的声称亦不足信。断言实业家因纳粹剥夺威胁在1938年后未再执行便可无视之,无异于宣称广岛与长崎核爆后“核选项”的停用意味着冷战期间无人应担忧核武器威胁,也或许这仅是后见之明。
此外,纳粹国家之所以逐步放弃布赫海姆与谢尔纳所关注的粗暴强制手段,实因1938年后对此类手段需求降低。典型案例的示范效应、恐惧氛围的营造,以及政企双方的经验内化共同促成了这一转变。试观以下演进历程:
1937年前,不配合政权目标的企业面临的终极噩梦是布拉巴格公司(Brabag)的强制组建;1937年后,则是在实质上没收矿场基础上建立赫尔曼·戈林工厂;而自1941年起,演变为成立大陆石油股份公司(Kontinentale Öl AG),这个旨在开发东欧占领区石油资源的公私合营企业,通过国家代表在监事会(supervisory board)与行政委员会(administrative committee)占据控制席位,政府持有足够多重投票权股份以确保政策主导权永久化。
在第一阶段,工业界反抗被法令粉碎,亚尔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动用权力迫使顽固企业为新公司注资;第二阶段,仅以法律指控威胁抵抗企业领袖便足以瓦解反抗;至第三阶段,所有企业都自动归顺并缴纳规定份额的运营资本,以求在占领区经济中分一杯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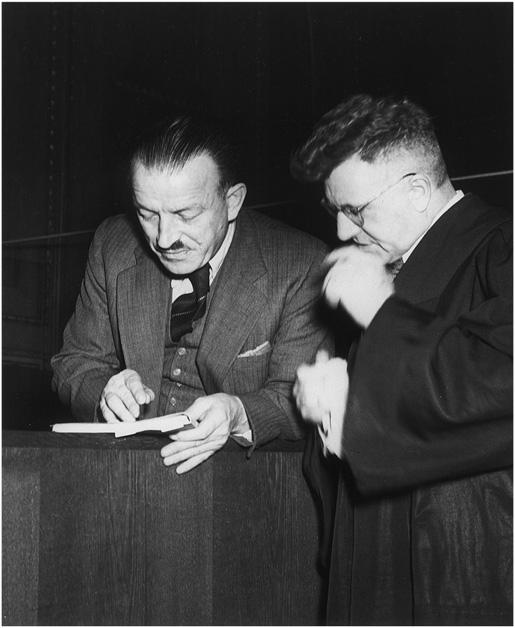
最后必须强调:当企业高管将纳粹国家的强制可能性纳入是否生产其要求物资的决策时,他们主要担忧通常并非国有化或其他形式的国家接管,而是市场地位或专业知识被更合作的竞争对手或新建国家支持企业夺走。IG法本公司在1930年代合成纤维领域的经历正体现这种抗拒的负面后果,因不愿按政权要求快速扩大产量,政府遂成立五家准公共融资地区合成纤维企业以达成生产目标并与法本竞争[15]。
对“国家授权竞争”(state-sanctioned competition)的担忧成为法本高管支持帝国扩张挪威铝产能计划的重要论据,正如1940年10月23日致公司主席信中所言:
我们认为若法本不把握当前机遇,赫尔曼·戈林工厂必将介入该领域。若此成真……我们将重蹈一战覆辙……当时最大冶炼厂劳塔工厂(Lautawerk)被国家接管,康采恩(即法本)铝产量被迫限制在20%。若有另一家国有企业进入该领域,我们的份额将进一步缩减。该企业亦必将涉足镁生产领域[16]。
类似地,1937-1938年间,因担忧国家可能成立“接管公司”(Auffanggelsellschaft)执行犹太人企业雅利安化,既有股份制银行加速为此类交易提供融资。在此案例(以及许多其他涉及国家干预前景的情形)中,真正令银行家恐惧的不仅是收益流失。他们更惧怕此类新实体无论成败都将带来恶果:若其成功则证明国有企业原则有效;若失败(尤其是政治影响资产分配时)则可能对前银行客户企业造成经济破坏[17]。
简言之,对纳粹政权单方面行动的后果之恐惧,无论这种恐惧源于国有化、竞争对手的创设与扶持、专利与工艺流失,抑或仅是政府笨拙干预对企业既有业务的损害,显然都极大限制了企业自主制定与推进发展战略的能力。以最戏剧化的方式表述:德固赛(Degussa)与法本公司(同意与国家合作开发炭黑(carbon black)与合成橡胶生产,固然因企业预期这些产品将实现长期盈利。但若两家企业的相关领导者未认定拒绝将危及他们凭借研发能力获取、并借国家支持建立的垄断地位,则毫无理由相信他们会以国家要求的速度推进,或屈从国家将工厂分别设于格利维采(Gleiwitz)与奥斯维辛(Auschwitz)的要求。事实上,大量证据表明相反情形。这些证据强有力地暗示:至少就化工行业大型企业而言,布赫海姆与谢尔纳关于“投资计划通常……源自企业自身而非国家规划机构”的论断需作重大修正[18]。
如先前所述,我认为布赫海姆与谢尔纳论证存在不足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于其分析现象的片面性。那些通过“纳粹国家阻碍的企业战略”而非“企业被说服服务或抵制的政府目标”视角审视政企关系的学者,呈现的第三帝国微观经济决策图景远非正常化。
这种观察角度使我认为:德国大型企业能够且在某些案例中确实失去了对自身产品结构的控制权,通过间接社会化过程沦为类公共或类国家实体,这一定性遭到布赫海姆的激烈反对[19]。我将通过两种方式论证此观点:其一聚焦1938-1939年纳粹政权与德固赛、法本公司互动的关键转折点;其二考察德固赛认为对其未来竞争力至关重要、但因政权限制原材料而无法扩产的一系列产品。

1938-1939年的转折点是一场波及德固赛与法本公司的严重流动性危机,因新工厂资本支出(主要为满足自给自足与军备扩张需求)不仅远超折旧额,且即将耗尽企业储备[20]。两家公司主席随即宣布紧缩策略,但这些措施迅速显露出力不从心。原因为何?答案在于国家对企业决策的渗透形式比布赫海姆与谢尔纳所承认的更为隐蔽。
法本的赫尔曼·施密茨(Hermann Schmitz)与德固赛的恩斯特·布塞曼(Ernst Busemann)无法遏制新设备开支激增,因其部分部门主管更倾向于借助国家支持扩张业务,而非关注企业整体财务健康。政权对自给自足与军备的强力推动分化了企业利益,在部分高管与特定政府/军事机构间缔结新联盟。这些联盟能够且确实打破了政企间关于产出战略的线性对立,代之以企业内部的博弈,其中与政府目标结盟的派系往往胜出。德固赛在1938-1945年间无法控制全资子公司奥尔公司(Auergesellschaft)的支出与负债(因其管理者获国防部(Defense Ministry)支持),正是此现象的长期例证[21]。
私营企业为满足国家强制需求而丧失投资控制权,是否足以将其定性为“类公共”或“间接社会化”实体(如我所言),学界可商榷。但即便目前仅少数案例佐证,该现象无疑削弱了布赫海姆与谢尔纳所谓“纳粹政权为企业制定生产与投资方案留有充分自主空间”的论断[22]。
至于德固赛受挫的扩展计划,其涉及1939年该公司商业优先级最高的三个业务发展方向。首项是新建金属钠工厂,该产品作为企业传统核心产品,用于金属硬化剂、氰化物、洗涤剂与漂白剂、四乙基铅、合成燃料及合成橡胶制造。第二项是新建过氧化氢生产设施,当时德固赛亦是该化学品的全国领先生产商,该物质对合成纤维制造、纺织品加工、多孔混凝土及若干新兴军事应用至关重要。第三项计划是大型综合性中央工厂,旨在将德固赛分散且陈旧的工厂整合至现代化厂区。
前法本公司雇员约翰内斯·埃克尔(Johannes Eckell)时任柏林化学工业主管官员,于1939年初德固赛提出申请时,拒绝为前两个项目颁发建筑许可与建材配额。直至1942年3月与9月(此时已无足够时间在战前建成工厂),其立场方有松动。德固赛因此认定:其在钠生产领域的优势已被法本取代,过氧化氢领先地位则让位于国家设立的工厂及政治地位更优的阿尔伯特·皮茨施(Albert Pietzsch)旗下企业——埃克尔在资源分配中始终偏袒这些竞争者。
至于德固赛规划的中央工厂,纳粹政权虽允许企业动用累积资本推进项目,却以“非战争关键设施”为由拒绝提供其他支持。从1939年11月批准立项至1941年底,项目几无进展;1942年重启时被迫修改方案,增加军用甲醛产量。尽管该设施于1943年末投产,但直至1945年3月苏军抵达时,工厂其余部分仍未完工[23]。
诚然,这些案例的延误因二战爆发而加剧。但关键点在于:决定德固赛可建项目与时机的乃是政府官员,而非企业高管;且该官员首次行使此决定权是在和平时期,基于纳粹国家已掌控的德国经济权限。
尽管布赫海姆与谢尔纳坚决反对使用“强制”一词描述纳粹主义下的政企关系,后者在某一段落承认企业确实面临“国家诱发的困境”[24]。据我所知,布赫海姆未使用此类表述,但其提供了该现象的若干案例[25]。此类承认部分缩小了我们之间的诠释分歧。即便如此,布赫海姆与谢尔纳的立场仍过于拘泥字面。
以他们关于“企业可通过出口传统产品维持原产(因政权重视外汇收入)”的论断为例[26]。此说在其论述框架内成立,但未提及第三帝国时期出口常无利可图,因帝国马克估值过高且出口补贴体系繁琐,德国企业单位产品国内利润普遍高于海外。换言之,选择出口以维持传统生产线虽是可行选项,却常缺乏吸引力,这也成为戈林在1938年威胁重工业任命国家专员以强制扩大出口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企业残存的产出选择自由完全仰赖政权许可。战争年代使此点昭然若揭,哈特穆特·贝格霍夫(Hartmut Berghoff)关于霍纳囗琴公司(Hohner harmonica)的杰作与迈克尔·施耐德(Michael Schneider)对三家开姆尼茨(Chemnitz)办公设备制造商的研究均证实此点。1939-1942年间,这些企业仅通过增产军需品才得以维持(日益缩减的)传统产品线[27]。换言之,纳粹经济政策形塑机遇,进而左右企业高管抉择。商人是否保有自由意志?当然。其自主性是否完整?我认为不然。
总结而言,我认为布赫海姆与谢尔纳挥舞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的姿态,宛如斯威尼·托德(Sweeney Todd)执刃,用比喻来说,其极端程度与后果亦不相上下。当他们以相当武断的方式削砍既有文献后,留下的是一幅将经济与政治割裂、对企业决策动因分析残缺不全、且将政企动态关系固化为静态的纳粹德国企业运作图景。
历史书写中的修正主义往往具有积极意义,但此案例提醒我们:当史学家着手修正历史记录时,需谨防矫枉过正。
作者介绍:
Peter Hayes是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担任西奥多·泽夫·魏斯大屠杀教育基金会(Theodore Zev Weiss Holocaust Educational Foundation)大屠杀研究讲席教授及查尔斯·迪林·麦考密克(Charles Deering McCormick)杰出教学教授。其研究专长为20世纪德国史,尤重德国企业与大屠杀关联性。